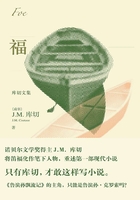突然,起风了。
风是从马路牙子那儿起的,紧紧贴着地皮,一拐一拐,漫不经心地画着小圈儿,好似婴儿头顶的漩儿,头发还软软地贴在头皮上,有些嫩嫩的黄,有些百无聊赖,看着都让人心疼。没有一丝丝声息,谁也没听到,起风了。
两个六七岁的男孩儿一人手里擎着一个氢气球,一个红气球,一个绿气球,从西边走过来,走得心无旁骛,只顾仰着脸看头顶的气球。下午的太阳好好地照着,照在红气球上,红气球泛着红光,映红了一张孩子的脸儿,照在绿气球上,绿气球泛着绿光,映绿了一张孩子的脸儿。那气球乖乖地碰在两个孩子的头顶,轻轻地一碰,又轻轻地一碰,他们小小的脸蛋儿便薄薄地红了,又薄薄地绿了。这时候,擎着红气球的孩子很乖觉,看到头顶的红气球动得有些厉害,有那么一点儿,想要挣脱开他的手。他愣了一下,看看另一个男孩儿的绿气球,那绿气球也像蠢蠢的小兽,动得有些厉害。他抓住另一个男孩儿的手,低下头寻着什么。
他们发现,起风了。
那风打着旋儿,像是奶奶在用一根棍棒不紧不慢地搅着热乎乎软绵绵的糖稀。旋儿沿着马路牙子走,一点儿都不慌张,旋得有一个面盆那么大了。在两个孩子的注视下,旋儿一直往孩子们的脚下走,孩子们让了一让,它又跟了过来,孩子们就不再让了,一面仍旧牢牢地擎着气球,一面低头注视着它挨近,眼睛睁得大大的,小小的嘴也微微张开了些。
那对沿着对面马路边的墙根朝东走近的母子却还没看到风。他们走在两个孩子的东边,风还没赶上他们。他们看不见,也听不见。
女人该有五十多了吧。很瘦,中等个子,看不见她的脸,裹着一块暗紫色的头巾,头巾看似有些脏,大概好几天没洗了。一缕花白的头发从头巾没裹严实的地方挑了出来,向外卷曲着,仿佛是,一根春天的常青藤,竭力地伸出腰肢,竭力去够着什么。随着女人铿锵的步子,那缕头发一扬一扬的,又仿佛是,在向着谁招手致意。女人伸手撩了一把头发,将它浮皮潦草地塞进头巾,只剩下中间一截憋闷地弓曲在外面。女人钉住脚步,转回头。
“走快点!磨蹭什么啊你?!”女人拧起了眉头。
这一瞬间,女人的脸露了出来。暗紫色的脏乎乎的头巾裹着脑袋,露出的只是一块倒三角形的黧黑的脸。看不到嘴,也看不到鼻孔,只看得到乱草似的窝着的额发,排满一梗一梗硬木橛子般皱纹的额头,还有,额头下那双小眼睛。那双眼睛本来就小,这时候,因为不耐烦,因为气恼,或许,还有别的什么,这一双眼睛愈加小了。
“快点儿呀!”
女人的目光尖尖地射出去,额头又皱了皱,似乎,额头上堆着的那一排硬木橛子就要因为这一皱而掉落下来一两根。
一个小伙子慢吞吞挨近了。
小伙子二十五六岁年纪,穿一双很大的解放鞋,穿一条很宽大的裤子,裤脚的后部踩在脚下,他专心致志地攥着裤腰,踮着脚尖,走一步,看一下脚下,走一步,又看一下脚下,生怕惊吓到了什么似的。他是担心脚后跟踩到裤子呢,可他每一脚下去,还是踩到裤子了。
女人喊了两遍,小伙子总算抬起头来了。他两眼茫然地瞅着女人,干脆站住了不走了,两只手仍旧没忘记攥住裤腰。
“裤带呢?!”陡然间,女人一声惊叫。
小伙子仍旧攥紧裤腰,茫茫然地瞅着女人。他一动也不敢动,只能那么踮着脚站着。
“我说裤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