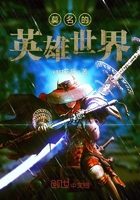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已包括,看的看,说的说,小城故事真不错,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作客……庞婉青的歌声很清澈,像是从遥远的梦乡悠悠地传来。她唱完了,向大家鞠了个躬,全场寂静,大约五秒钟之后,大家才想起来应该鼓掌。于是,掌声像暴风骤雨一样地响起。廖强生也使劲地鼓掌,他突然从桌上端起两杯酒,走到她面前递给她一杯,说:“谢谢你带给我们优美的歌声。”
“说什么呀,我要谢谢你呢。”庞婉青害羞地低下头,把酒喝了,然后对大家说:“下面我提议,我们合唱这支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好不好?二十年前,我们唱着这支歌,二十年后,我们再来唱这支歌!”
大家一致叫好。银幕上出现了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音乐响起,大家扯开嗓子,拼命地提高声音,唱歌已经不像是唱歌,而是吼叫,摇头晃脑地吼叫,手舞足蹈地吼叫,似乎要把心里所有的一切全都吼叫出来。这支二十年前的歌曲,曾经是那样的激荡人心,二十年后用一种别样的心情吼叫出来,令人仿佛穿越时空隧道,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不停地穿梭往返。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酸甜苦辣,所有的光荣与梦想,所有的成功与失败,所有的一切,全在这从内心里吼叫出来的歌声里: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奇迹要靠谁?
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
啊,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自豪的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歌声有时高高低低参差不齐,有时又洪亮有力整齐划一,高亢、激越,最后一句像惊天动地的海啸,从高高的地方砸下来,然后散开了,化作一滩水沫,好像青春期的终结。许多人都流下了滚烫的热泪,裴慧洁已经泣不成声,只能走到一边,不停地耸动着肩膀。庞婉青走到了她的身边,搂住她的肩膀,紧紧地搂住,像大人鼓励孩子一样,所有的话语全在那温柔而又刚强的动作里。
歌声停住了,全场静默了十秒、二十秒、三十秒,仿佛一个时代的远去,大家全都在默哀之中。
还是刘老师按捺不住地走了上前,他满脸红扑扑的,闪烁着酒精的光芒,好像也回到了过去的青春岁月。他呼了口气,拿起话筒说:“我……”他又抹了一下眼睛,这回真抹下了几滴眼泪,他眼光闪闪地说:“二十年很长,二十年也很短,有相聚,就有分别,只在同学在,那份情就在!”
大家纷纷点头,都不乱喊乱叫了,只是点头,也许还没有缓过那口气来。
刘老师接着说:“下面,我想继续我们刚才的小节目,不过稍微改变一下,由在座的同学随便说一个座位号,让我来猜出谁的名字,我要是猜不出,我罚一杯酒,我要是猜出来了,你们大家喝一杯酒,怎么样?”
好,好,几个粗嗓门先响起来,大家这才缓过气来,纷纷叫好。有几个声音便叫了起来:48号!48号!刘老师挠了一下脑袋,立即说道:“王艺芳!今天没来,原因是孩子太小,刚满月。”他像孩子一样得意地笑着,指着大家说:“来,你们请自饮一杯!”
有人自觉地喝了一杯酒,有人只是轻轻抿了一口就放下了酒杯。一个尖嗓子叫道:34号!刘老师不假思索地说:“阎顺利。我坐过他的车呢。”阎顺利被旁边的同学推着站了起来,他手上端着一杯酒,先把酒喝了,神情紧张地说了一句:“谢谢老师,谢谢同学们。”
22号!又一声音喊道。刘老师脱口而出:“江全福。我这个班主任还算是称职的吧,二十年了都还记得。”江全福脸红耳赤地端起一杯酒,一口喝了。
下面一个声音突然叫道:14号!几个声音立即附和起来:14号!14号!
刘老师愣了一下,脸色好像沉了下来,他令人不解地走到桌前,端起一杯酒,把酒洒在了地上。
大家奇怪地看着刘老师,感觉刘老师像是霎时变了一个人。他缓缓地洒下一杯酒,语调低沉地说:“14号李跃鹏同学,永远不能来了,这杯酒献给他。”
大家立即明白了过来,放纵的心里多少有了一份沉重。
这时匡老师突然站起身,说:“对了,我想起来了,还有个路安远同学,他在大学毕业时失踪,也不能来了,可惜呀!他以前老爱我跟争辩的,唉,我劝他面对现实一点,他总是不听。”邹老师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总是不理想。”匡老师点点头,沉重地叹息一声,端起一杯酒,洒在了地上。于是大家纷纷效仿,随便端起桌上的一杯酒,也不管是谁喝的杯子,全洒在地上,让他们的老同学路安远也好好喝几杯——也许他能喝到的,谁知道呢?大家的表情有些游戏,有些庄重。
地上酒水横流,像无数条小河。
外面的风雨依旧在呼啸,里面却风平浪静下来了,好像翻江倒海过后,大海上出现短暂的安宁。许多人不胜酒力,体力也严重不支,亢奋了这么久的时间,全身都感到了疲乏,需要好好地歇一歇了。个别酒力体力均佳的人找不到对手,也显出了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寂寞,有人萎靡不振地耷拉下脑袋,打起了瞌睡,有人想吐而吐不出,哇哇哇地干呕着。桌上杯盘狼藉,但有的菜还是原封未动,桌下酒瓶子横七竖八,酒水四溢。
这时,餐厅大门里走进一个身躯佝偻的老头,他穿着一件长长的雨衣,雨帽翻了下来,两只眼睛瞪得大大地打量着酒桌上的人们。
一个服务员朝他走了过去,询问他来干什么?
老头目中无人地瞄了服务员一眼,从口袋里掏出一封弄皱而且淋湿的信,说:
“二十年后的聚会——马铺一中85届文科班同学会,我来找找我儿子有没有在这?”
老头说话嗡声嗡气的,像是年代久远的唱片发出的那种声音,但是每个字都咬得很准。
离他最近的刘老师听了,不由心头一颤,他上上下下看了看老头,只见这来历不明的老头脚步蹒跚,两只眼睛瞪得像电灯泡一样,闪着一种倔强、魔魔怔怔的光,嘴上有一撇蓬乱的胡子,已经全发白了,被风吹得一抖一抖的。
“老大爷,你要找谁?”刘老师问。
“我要找我儿子,看看他有没有在这?”老头神神道道地说着,似乎很不屑和他多说什么,就向那四张酒桌走去。
那边桌上的人们全都歪歪斜斜地坐着,有的像泥巴一样糊在椅子上,有的喘着粗气发呆,有的晕晕乎乎地打着瞌睡,一个下午又叫又唱又闹的,他们全都累了,还有几个男同学比划着手,在争论该怎么拼酒,还有几个女同学咬着耳朵在说什么悄悄话,还有一个男同学想用左手跟一个女同学扳手腕,被谢绝了,还有一个男同学满身酒气地站起身,向卫生间踉踉跄跄地颠去。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一个老头走近了,并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盯着他们,一个一个地瞄过去,在他们中间寻找着什么……“哎,老大爷,你到底要找谁?”刘老师走过来说。
“我要找我儿子,看看他有没有在这?”老头说。
他的眼光已经扫过一遍了,这些无精打彩像是被抽去了灵魂的人里面,没有他的儿子。这些人,男的一个个脑满肠肥、方头大脸,女的一个个花枝招展、红唇白脸,他看着他们摇头,喃喃地说着呓语:“我儿子高高、瘦瘦的,还没怎么长胡子……”
老头失望地扭过头。在他看来,这些人目光麻木散淡、表情浑浑噩噩,像是放纵在花天酒地中的饕餮之徒,他儿子才不是这样的人,他儿子二十岁,高高的,瘦瘦的,目光很刚毅,嘴上开始长胡子了,但还没怎么长。他失望地缓缓地转过身,走了。
一个打瞌睡的男同学突然惊乍地跳了起来,他看到老头佝偻的身影,好像看到鬼一样地尖叫一声。许多人受了惊吓,唰地振作了精神,有人就问怎么了怎么了,有人就骂骂咧咧的,有人就打着呵欠,做演讲状:同学们——“那老头不就是路安远的老爸吗?”一个男同学指着老头的背影说。
路安远?!大家全都来了精神,有人跳了起来,有人直起腰,有人瞪着眼睛呆住了,大家看着那老头的身影消失在门口了,一阵苍凉的脚步声从楼梯下去了。
路安远不是在大学毕业那年失踪了吗?他老爸居然跑到同学会上找他来了!大家都知道,路安远的父亲十多年来没有放弃寻找他的信心,他几乎每天都在寻找,在别人看来,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人,一个失去正常理性的人。他总是在寻找,他居然寻找到同学会来了,他当然找不到,他儿子是个高高瘦瘦的还没怎么长胡子的二十岁的小年轻,而这里全是身心疲惫的四十岁的人,所以他找不到,不得不失望地匆匆地转身离去。
大家恍若梦中。突然有人跑到窗边往外看,许多人就围了过来,唧唧喳喳,指指点点。路安远当年就是班级的一大怪人,现在他的父亲也成怪人了,真是怪、怪、怪……他们看到路安远的父亲走在狂风暴雨中,弯曲的身子像一张弓,随时有可能被吹走,他走得那么艰难,几乎不像是走,而是在爬。这是怎样一个坚忍不拔的父亲!大家想,路安远同学没有来参加同学会,他父亲来了,我们也应该请他坐下来喝一杯酒才对呀!刘老师、顾明泉、汪洁丽、庞婉青还有廖强生、陈炳星、罗汉城、陈朝阳等等,都跑到了窗前往外看。路安远父亲的影子在晃动,好像只要风雨再大一点点,就能够把他连根拔起地吹走。大家说,应该把路安远的父亲追回来才对呀!那是我们同学的父亲!可是,话虽这么说,在场的每个同学目瞪口呆,神思恍惚,谁也没有行动。
这时,外面的风更猛了,雨更大了……
2005年9月15日至11月7日写于南靖温泉2005年11月12日至18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