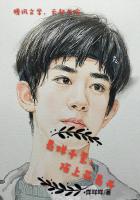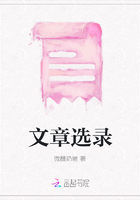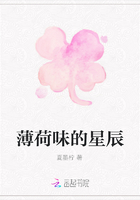沈从文1949年3月13日给张以瑛的一封信也像是一篇“绝笔”。他讲了自己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自我意识。“我因过去生命限制,小时候生活受挫折过多过久,心受伤损。从‘个人挣扎’方式中战胜困难,支持下来,因之性情内向,难于与社会适应。而个人独自为战精神加强,长处与弱点即在一处。如工作恰巧和时代需要相配合,当然还可为国家下一代作些事。但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工作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这长处如果又大多是‘抽象’的,再加上一些情绪纠缠,久而久之,自然是即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持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也就是目下情形。”(《致张以瑛》.《沈从文全集》19卷.19-20.)“我执”形成的原因是因为沈从文经历了异常艰难的个人奋斗的人生历程,一切都是靠自己一点点得来,一点点形成的。用他的话说是“个人挣扎”,是“顽固”,是“作茧自缚”。他充分感受到了其所带来的孤立。
《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写于1949年3月6日。他在这篇文章末尾自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解放”指“解脱”)。3月28日的时候,他自杀了,但没有死。那么这篇文章无疑是“绝笔”。文章表达了他希望自己能改变得适应新的要求,但很难说服自己心灵的矛盾和痛苦。在这篇文章里,沈从文依然坚持着自己。他自信自己作品的不合流俗,他只是用音乐和美术来表现人生和生命,拒绝别人从中寻找什么思想和哲学。他依然强调都市与乡村的对立。他依然相信只有艺术可以拯救他的生命。他说只有音乐能对“我”的生命起到调和作用:“认识我自己生命,是从音乐而来。”“一个有生命有性格的乐章在我耳边流注,逐渐浸入脑中襞折深处时,生命仿佛有了定向,充满悲哀与善良情感,而完全皈依。音乐对我的说教,比任何经典教义更具效果。也许我所理解的并不是音乐,只是从乐曲节度中条理出‘人的本性’。”这种完全唯美的人生态度,与越来越强的政治态度的要求完全悖反。他所信仰的还是美。但他对现实又充满渴望,他希望自己还能融入新的世界,他甚至为自己找了一条路,即从事文化研究。他从文学投入向文化关注的转移,始于云南。在那里,他发现了“剩余潜伏文化”的价值:“即由西南文物的残余,为历史所忽略,亦未曾为现代学人注意过的东西,保留了点新印象,得到些新启发。”他谈到他对西南文化研究所作的充分的准备,透露出他希望自己能有新的价值的信息。他的生命价值本来可以实现顺转。但他感觉到现实的压力不会给他机会,他体验到强烈的绝望之情。他觉得自己多年前作品里所写到的悲剧竟成了自己命运的预言:“塔圮了,船溜了,老船夫于一夜雷雨中死了,剩余一个黑脸长眉性情善良的翠翠,在小河边听杜鹃啼唤。一个悲剧的镜头如此明白具体。”自己的生命也走到了这个绝境。人被自己的预言击中,瞬间的绝望是难以述说的。他呼喊:“我应当回到我最先那个世界中去,一切作品都表示这个返乡土的诚挚召呼。‘让我回去,让我回去,回到那些简单平凡哀乐中,手足肮脏心地干净单纯诚虔生命中去!我熟悉他们,也喜欢他们,因为他本是我的一部分。’”(《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27卷.)这种回去的呼喊是他最绝望的声音。他觉得自己无力走出这精神的泥潭,准备把生命交付给死亡,让完全的黑暗来终止这痛苦的选择与被选。
他思考的另一个理由是自己太忽略了“群体”的力量。沈从文一直是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典范,在各种论争中也一直是在个人作战。他认为只有以个人的名义,出于个人的思考才是最光明正大的。由郭沫若引头而起的这场精神围剿让他强烈地感觉了他以前一直忽视的“群”的存在和力量。他也意识到了,新时代所要求的就是个体向群体的归依。这对于一直坚持用怀疑的态度来保持自己的警觉和判断的沈从文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从“我”走向“我们”,对他来说是异常艰难的。但他慢慢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他最先的感觉是自己被“群”抛弃的孤独:“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独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沈从文全集》19卷.)他意识到“群体”的重要性,也感受到了被群体抛弃和隔绝的孤独中恐惧。对于沈从文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怎样认识群体的力量,怎样进入到群体当中去,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能够进入这个群体的,各自已经找到了途径。在时代的大变动当中,很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了只有依靠民族群体的力量才能真正解放这个民族。知识分子也要进入到这个群体当中。我们上文已经谈过这一点。他们的图景是时代的风雨标示给他们的。对于沈从文而言,他并不相信所谓的群体,也不相信革命。他信赖的是专家学者,对文学,对国家民族而言,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希望。新时代的到来是强制性地要他转变这种观念。个人精神的孤独已经不能再给他带来心灵上的优越感,而是对生存的深深忧虑,生成了一种艰难的挣扎。他开始承认:“人无从离群。”也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与群体的游离,在给很多的人信中,他都提到了自己与群的游离造成了在新时代的毁灭。他还无法确定“群”的确切含义,但他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了它的威力,也感受到自己必须向这样的群体靠拢。他知道新时代“要求于人的是‘忘我’‘无我’,忘掉或去掉那个小小的,蜗缩的,有限的我,而将‘我’溶解于政治进程中,社会要求中,或者说,一个‘为下一代合理、进步、幸福’大原则中”。他已经感觉到,在新的时代,人们的生存与社会与政治的联系会更加密切。人们不能再“执我”,而必须学会融合,学会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视野中来衡量自己的存在:“这检讨虽出诸自己,决定却属于外缘,‘人’、与‘时、’与‘事’。我应当完全放弃我之为我处,委生命于人天。我已深深体会到人与人的不可分割性,相关性,连续性。‘我’是否重要,在于对将来多数的人是否还有意义或影响。”(《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27卷.)他用自己的思路发现了问题的核心:个体生命的价值必须接受时代和社会的考量。但从其表述可以看出来,他所说的“群”也是他个人化的一种理解,并不等同于那个时代的“群众”含义,而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他是迫于压力思考个人和群体的关系的,并不是他从心里接受了这种观念。
沈从文渴望“新生”,对他而言,新生就是“得回了我”。“雨雪漉漉,见日则消”,新的一切就像太阳一样有生命力有力量。他说他已经完全相信了新的一切,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向人民靠拢才代表着历史的方向。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面临回归人民的问题。“出于个人问题,对现实或承认,或否定,总之随处随事都必然会有广泛的消耗与牺牲。一切平时与人民生活隔离的知识分子,既首当其冲,对革命来临以后如何自处,自然感到极大的苦闷与彷徨。”这是知识分子“一个相当困难的心理疙瘩”。因为这涉及到了思想问题,“既涉思想,即有根深蒂固连续性,顽固排他性,不仅限于‘当前’,还要检讨‘过去’,防止‘未来’。”他希望负责方面对知识分子“莫取压迫态度”,才最有利于他们的“新生”(《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27卷.)。《一个人的自白》是他试图用新的观念来解释自己人生和创作的一种努力。因为他说:“就我近一月所接触的各方面问题和事实看来,我已完全相信一个新的合理社会,在新的政府政治目标和实验方式下,不久将来必然可以实现。”但这些观念的借用依然充满了他个人理解的意味。“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新生”的含义是获得认可,个人价值得到承认。“我必须为一个新国家作一点事!我要新生,为的是我还能在新的时代中作一点事。”“新生”意味着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给我一个新生的机会,我要从泥沼中爬出,我要从四月五日《进步日报》辛群一文中认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种种过失,从悔罪方法上通过任何困难,留下余生为新的国家服务。”“新生”需要的首要条件是“悔罪”。实际上,沈从文认为真正的“新生”必须是重新找回自我,“得回了我”,“我的生命似乎在转变了。我理会到这个过程。我的教育已浸入生命深处。我有了新的信心,对当前的主宰有了深的信心。生命似乎得到了调和与清明。看事明白多了。我得接受他人给我的死亡或新生。我的幻念即依然尚保存于一个活活的头脑力,我将用到另一方面去,不在个人问题上缠绕了。……我似乎已得回了我。用这个我来接受牺牲,或接受新生,都坦然泰然的。……惟属于自省,可能有些发展情绪经验是由一个过程,由胡涂,自蔽,以及一切性格上的矛盾,经验上的矛盾,理欲上的取舍,经过个人一个相当长时期清算和挣扎,终于明澈单一,得回一种新生。这过程是相当复杂辛苦的。……到这种明澈为我所有时,我觉得我对一切,只有接受,别无要求了。”(《四月六日》.《沈从文全集》19卷.25.)
在太过孤立的时候,他用书信的方式向朋友求救。这期间他写了两封求助信。一封给刘子衡,另一封给丁玲。刘子衡是曾经与他在青岛进行过雪夜长谈的挚友,他信任的人。给他的信,主要是倾诉,倾诉自己此时的心境。他还是强调自己的悲剧命运是因为与群体的游离,一直拒绝任何群体的束缚。“一个与群游离了二十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解放北平本来是件大事,我适因种种关系荟萃,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方合事实,因之胡涂到自毁。”外界给他的否定给他的心灵造成毁灭性的压力。他说到自己最大的悲剧是“吾丧我”。也就是在外界的否定的声音中无法相信原来的自己,自己的观念和信仰。他亲手撕毁了很多自己写的,自己原来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那许许多多写下的自以为值得保留的,或别的原因要保留的,全撕毁了。”从外在的否定到内在的怀疑和否定,他不知道哪里是自己的立足之地。他说自己的生命是“一堆碎瓦”。没有人再认可其曾经“宝玉”一般的价值。“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隔成忌误,即家中孩子,也对于我如路人,只奇怪又发了疯。难道我真疯了?我不能疯的!可是事实上,我可能已近于半疯。”他已经非常独立,被“疯狂”的想象紧紧纠缠着。“我因之心受了伤,永远在抽象恐惧中,及近于边际刺激迫害中,不知如何方能挣扎出这个缠缚。”沈从文一向是过去重视精神生活的,用他的话说是在抽象中游泳,往往有不能回头的感觉。在面对外界的精神压力时,抽象的恐惧对他而言也如深水一样要将他淹没。他说自己想重新加入群中,以实现自己的重造。他想向朋友征求意见,自己究竟有没有可能,“在我明白离群错误以后,是不是还能有新的生活可以重造自己?”(《致刘子衡》.《沈从文全集》19卷.)他非常渴望从朋友那里得到一点认可。这种非常绝望的倾诉有利于疏导他沉陷于抽象的恐惧。另一封信给丁玲。在1949年3月13日给张以瑛的信中,他希望能有人理解他。压力是来源于政治,所以他希望那份理解能来自一个代表着组织的人。他想到了丁玲,她既是共产党的文化方面的领导人之一,又是自己曾经的好朋友,是最合适的人选。“但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共产党如果要的只是一人由疯到死亡,当然容易作到。如以为我尚可争取改造,应当让我见一见丁玲,我亟想见她一面。”(《沈从文全集》19卷.19-20.)丁玲是左翼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又曾是他非常好的朋友。从朋友的认可到党的认可,这是他的思路。他在自己最难的时候想到她,这就使后来的那场恩怨更加让人难以理解了。在致丁玲的信中,沈从文表达了自己因为离群而导致的崩溃。自己虽已成了一个难以粘合的破碎瓦罐,但仍在努力“退思补过”,在改造自己,在努力粘合自己,希望丁玲能向上面转达自己的意思,中共能谅解自己,能给自己一个“向人民投降”的机会,得到新生。他决定完全放弃自己,“已找寻不到什么是‘自己’的思想成见”,“为自己,我已痛苦挣扎了近四十年,永远如独自作战,实在太累,得休息,也不为什么遗憾了”。希望通过这样“彻底”的改造,自己还可以为新社会“垫一块砖”。他的改造真正实现了的一点就是向人民的靠近和回归。在给丁玲的信中,沈从文自我检讨的声音就更为明确了。他甚至提到了再没有什么自己的思想成见,“抛掉自己过去越快越多越好”,提到向人民投降,提到“完全敬爱政治上一切领导设计,并积极参加”,提到学习“中共好榜样”,提到彻底改造。他没有敢把丁玲当做真正的朋友那样交心,只是希望丁玲能看在曾经的友情上向上转达他的愿望,“我盼望你为公为私提一提这一点”(《致丁玲》.《沈从文全集》19卷.)。他是把丁玲当做组织那样来检讨自己的。尽量用新的语言,新的价值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不是沈从文真正的心理,最真切的是希望通过一切的努力来重新获得在新时代的一点位置。
三、形象化的思维和表述
沈从文这些自白、日记和书信所呈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都是形象化。在这种时代转型的阶段,知识分子的精神转型,思考的核心应该是“思想”的转变。但沈从文一如既往地厌恶“思想”,他思考的核心是“生命”。“生命”在他恰恰强调的是排斥“思想”而张扬心灵和情感。“生命”和“新生”指向的都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调整,是心态上的接受而不是思想的改变。“生命”本身在他的思维中就是一种活的,美的,应当被肯定和赞赏的存在。比冷冰冰的思想对人的重要性大得多。他非常形象地把自己的“思想改造”想象为一种实体性的“摔碎”和“重铸”,称通过改造而获得认可为“新生”。这样的思路让人们感觉整个思想改造的过程对他而言是一场活生生感受得到的死亡之旅。他因此常常提到死亡,并且亲历了一次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