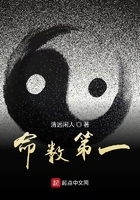小白龙冷哼道:“原来如此。他既憎恨萧绎,想来之前的效忠都是假的。怪不得了,他隐藏这么久,竟是为了他自己一片江山。那萧绎还以为自己利用了他,殊不知他早被这萧慕理捏拿在手!随时死无葬身之地!”
楼氏叹道,“也怪不得王爷如此。王妃您是不知当年王爷中毒多深。若老奴没记错,王爷十岁那年曾亲口告诉我,他中的这毒有多深,他对萧绎和薛志的恨便有多深!终有一日,他定会如数偿还!”
“那时老奴虽心疼王爷,但想到小孩天真无邪,过了明天便忘记今天,便未曾将他的话放心上。孰知……这孩子竟真下的了手?”
“他如何了?”
“小王爷跟着鬼医郎君治病之时,日日钻研在草药之中,当时我们还以为他想早些治好病,谁知,他竟是在苦心钻研如何将所有药物的药效发挥到最毒却又不致死的方法!”
小白龙身子一凉,诧异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楼氏点了点头,”王爷研制了很久,却也不知为何,未将这药物用在萧绎身上,竟还去效忠他,跟随这人。”
不似楼氏的惊讶,小白龙却是看的明白,苦笑道,“他需要报仇,又需要江山,还最会伪装,自然要借用萧绎这一颗棋维持这南梁江山不成飘萍。依我看来,如果没错,狠绝如他,自是不会放过萧绎。这药,早晚会用在这七皇子身上!”
楼氏不加评判,道:“老奴不知这药物是否会用在七皇子身上,但我知,这药,他用在了另一人身上!”
“另一人?”小白龙捻眉,似是在思索甚么,忽然豁然开朗,回复一片清明,“月袍将军薛典,乃薛志的亲人?”
楼氏听得小白龙这么一说,老眼亮丽,心头佩服这瞎了眼的女子思绪转弯快,脑子机灵之至。
“正是。”楼氏说道。
“薛典乃薛志最为珍贵的独子,年少成名,文采斐然,温文儒雅,智谋绝佳,还有一双天下无双、极其敏锐的千里耳。所以,薛将军是当时萧族上下唯一能和王爷齐名的孩子。只是可惜这薛典并非皇族之人,否则,以薛典之能,不难成为第二个秦淮王!”
小白龙这下明白这二人之间某些渊源,道:“莫不是,那厮眼光犀利,想要复仇,不直接找薛志,反倒是找上了他儿子?”
楼氏应了声,“待丁令光被人奸杀,裸尸于王朝上下的第二天,当时年仅十五的薛典亦是走了厄运,突着恶疾,身体器官差些全数腐烂,幸亏得他身为御医的父亲薛志所治,勉强活了过来。”
“这恶疾是萧慕理弄的?”
“嗯。这可是王爷潜心研制了三年的药物,聪明如他,怎会让仇人这般好过?”
“薛将军就成了这般?”小白龙问道。
楼氏瞟一眼这瞎眼女子,颇有叹息,沉吟良久,道:“若真只是如薛将军如今这般模样便好了。”
这话言下之意小白龙哪里听不出,冷冷问道:“薛将军如今这般弱不禁风,还不够?难不成还有甚么……”
“还有甚么?”楼氏苦笑道:“还有的,竟是薛家苦苦隐瞒,众人不知但王爷和老奴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那薛将军,威名赫赫,名震天下,不仅弱不禁风,还有……还有……”
楼氏迟迟不开口,惹得小白龙更是心急,但却未曾表现明显,淡淡道:“还有甚么?”
“那薛家香火,从薛典这里断了!”楼氏唏嘘说道,小白龙面目讶然,“薛典他……”
“是了。那便是王爷想要的结果。这薛将军,人中俊杰,如今不但身体羸弱,更是不能生儿育女!”楼氏凑到小白龙面前,低声呢喃道:“这事只有王爷知道,老奴也是在偶然间得知的,别人无人知道,此时多嘴才说了,王妃可得守好这秘密。”
小白龙走神之际,听闻此话,冷笑道:“以那厮狠绝,定希望这消息散播出去的好,怎么会甘愿隐瞒?”
“这也不知。但薛家却是清楚明白,这毒是谁给下的。因为,王爷从未隐藏过此事!”
“怪不得了。那人竟还有这么一大段曲折。”小白龙幽幽一叹,脸上不知是落寞还是甚么,冷笑道:“复仇,不去伤害本人,而是将那人最爱的人给伤地彻底!果然是聪慧绝伦的南公子!秦淮王!”
末了,小白龙徐徐叹道:“这等断子绝孙的仇恨!怪不得,那夜他死活不答应自己的请求。”
“甚么请求?”楼氏不解这小白龙言下之意。
“没甚么。看来,这南梁江山,无论是从前,还是将来,本应是他的。”
“是了。王爷曾迫不得已,将江山拱手相让,深藏不漏韬光养晦数载,如今,是该收回来了!潭中卧龙,不可能永久沉睡地!”
小白龙一直明白这楼氏能当那人的奶娘这么久,自是有些见识,不可小觑,但此时听得她这么一句,依旧没想到这一个下人能说出这般话,心头对这老婆高看几分,“只是,他这人哪……江山一回袖,冤血几多流?”
“王妃,今夜说这么多,是老奴嘴贱,不过是希望您能多多体谅王爷的苦衷。他年少被流着同样鲜血的亲人害死了父亲、兄弟,看着母亲为自己治病而被人打死,又被至亲因为皇位而下了毒,王爷若不狠绝无情,若不伪装隐藏,若不是这般精于算计,如何活到今日?又如何成为和您齐名的四公子?又如何登上今日高座?来日又如何征战天……”
“罢了。”小白龙挥挥衣袖,面有疲倦,“奶娘,你放心,今夜你的话我都只记心里了,绝不告诉二人。但现下我有些累了,可否让我歇歇去。”
奶娘正要再说,见小白龙那面容疲倦,道:“那王妃可要好生休息了。这鱼汤冷了……”
“罢了,你自离去,鱼汤冷的,也是滋补的。”小白龙懒洋洋说了这么一句,躺于卧榻之上,双手枕在脖颈之下,似是在思索甚么。
楼氏看她一眼,摇了摇头,径自离去。转瞬,屋子里便只剩了那一道孤零零的白影。未曾闭眼,神色间是难得的平静。
“南边的,原来,你我皆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