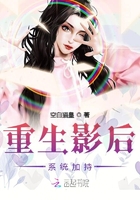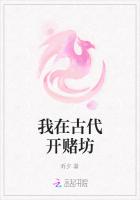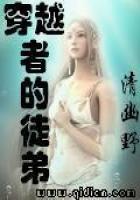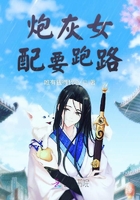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蔡仪先生就不倦追寻革命。一九二六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血气方刚,风华正茂,被热火朝天的革命气氛所感染,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曾说,同宿舍的几个同学何允汉、文心金等等,都是团员,经常分头或一起到北大附近的工人夜校进行宣传,为他们讲课。问题不在形势好的时候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而在于一九二七年革命形势恶化,李大钊被捕,共青团组织停止活动,蔡仪先生的一些革命同志失踪的失踪,被捕的被捕,杀头的杀头……--这样的时候,以前革命的人纷纷离开了,遁入书斋或销声匿迹。蔡仪先生不,北方不行,他去南方。他于一九二七年春带着团员介绍信,经天津,过上海,到武汉……寻找组织,寻找革命,这中间发生了许多故事。据蔡仪夫人说,一九二七年,蔡仪先生南下寻找革命路经上海,在街上看到一个叫化子模样的青年,腋下夹着一卷破席,忽然用英语向他问道:“你是从北京来的学生吗?”蔡仪先生回答:“是。”那人说,他是清华大学学生,流落于此,本要到江湾去找他的哥哥,身上没有一文钱,希望得到一点帮助。这个青年为了使蔡仪先生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还说,清华图书馆的地板是钢化玻璃的,还有游泳池,蔡仪先生正好也去过清华,知道他所言不假,于是相信他确实是清华学生,就把他带到自己住的旅馆。在旅馆门口,那青年人迟迟不肯进去。蔡仪先生说,你是我的客人,没有关系,请到里面坐。蔡仪先生不仅让他在自己房间休憩,而且还让茶房买来一碗牛肉面请他吃。临走,问他需要多少钱?那青年人说,到江湾的路费,只要三元。蔡仪先生给了他五元。蔡仪先生后来说,那时北方学生到南方来寻找革命者很多,即使萍水相逢,也应竭诚相助。他坚信那位青年是为革命而来南方,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流落街头的。但最终没有接上组织关系,很失望,很苦闷,只好回乡教书。
一九二九年,蔡仪先生于苦闷、悲愤、无奈之下去了日本之后,他的“寻找组织、寻找革命之心不死”,据蔡仪夫人说,他还曾企图寻找日本共产党--也许今天的年轻人看了好笑:怎么追求党、追求革命,追求到日本去了?你不知道:“共产国际”嘛,那时的革命者心目中,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是一家。请看,这就是蔡仪。真是“革命之心,矢志难改”啊。但是,当时日本也处于革命低潮,共产党倍受打击,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到一九三三年小林多喜二因拒捕而被杀,共产党组织被摧垮。蔡仪先生虽没找到日本共产党,但他一直关注并参与日本马克思主义运动,成为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成员。
一九三七年蔡仪先生回国,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后,蔡仪先生取道天津南下。火车到天津,日本人要检查。日本兵非常野蛮:“站好!不许动!”蔡仪先生十分气愤。日本兵说的是日本话,蔡仪先生听得懂,但站台上几百名中国同胞听不懂,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按常理,在这样的时候,为躲避麻烦,尽量不要出头露面,混过去,走人。但蔡仪先生看不得日本人折磨自己的同胞,站出来,把日本人的话翻译出来,并大声为自己的同胞讲话。日本兵看到蔡仪先生竟敢在这种场合大声为同胞说话,还懂日语,于是先把他扣起来,审讯,推打,侮辱。后来在他身上翻出九州帝大的学生证,才把他放了。
蔡仪先生很快马上投入抗日活动,而且不遗余力。在三厅,他是在一群共产党人周围参与抗日活动的。很快,大约是四十年代初,他就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一九四五年入党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而且没有预备期,直接成为正式党员,其兴奋,可想而知。他把加入中国共产党视为一生中最重大的事情。此后,蔡仪先生忠心耿耿跟党走。
解放后,大约是一九五四年,一向温和的蔡仪先生发了一次火,表现出他在原则问题面前的强硬,而且是同他最好的朋友杨晦。当时的教育部要蔡仪先生为“文学概论”拟一个提纲,作全国文科教材使用。提纲拟好了,教育部说要开会讨论,由蔡仪先生主持,就在他家楼下。参加会的,有教育部的代表,有北大的杨晦、钱学熙等先生。那时,正好是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来北大讲学,有一个“文艺学引论”提纲。毕达可夫何许人?不过是莫斯科大学的一位讲师,算不上什么权威,即使权威又如何?然而,蔡仪先生主持的这个讨论会进行到第三天,杨晦先生说,应以毕达可夫的提纲为准,要讨论,就讨论毕达可夫提纲。蔡仪先生很恼火:教育部要我拟的提纲,又由我主持讨论会,我拟的提纲自然应该参加讨论。蔡仪先生说:“何况我对毕达可夫提纲还有不同意见呢!”杨晦坚持:“当前学习苏联是党的政策。”于是两人争执起来,互不让步。虽然杨晦先生是蔡仪先生的老朋友、好朋友,而且年长蔡仪八岁,蔡仪一向敬重他,但这次,却是“寸土必争”。
六十年代,一次在露天的中山公园音乐堂看话剧《刘胡兰》。正当演到刘胡兰就义时,反派演员出了点儿小差错,观众中有人发出“吃吃”笑声,与剧中气氛、特别是与观众此时的心情极不协调。听到这笑声,平时不言不语的蔡仪先生愤怒了,而且他的愤怒像火山爆发,霍然站起,大声吼道:
向革命烈士学习!
向革命烈士致敬!
这吼声变成了口号声,在剧场回荡。接着,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起立致敬--向烈士,也向蔡仪。
乃“性情中人”也
蔡仪先生最初是学哲学的,后来又长期从事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研究,写大篇大篇抽象思维的文章,出大部大部逻辑严密的着作,成天同概念、判断、推理打交道,总喜欢从那些纷纷攘攘、变幻无穷的现象世界中提炼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来,所以给人的印象是“极富理性”而“缺少感情”。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一次《人民文学》编辑部开座谈会,一位专写散文和报告文学的老作家坐在我旁边,指着正发言的蔡仪先生悄悄对我说,我真想写写他,看他是怎么思维的--他脑子里叫理性概念填满了吧?感性、感情,经他的理性阳光一晒,蒸发没了。
这当然是错觉。看起来只会抽象思维、“用理性蒸发了感情”的蔡仪先生,乃“性情中人”也。接近蔡仪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他和夫人乔象钟生有一子二女。唯一的儿子小豆,身染不治之症,小小年纪即瘫痪在床。蔡仪夫妇为给儿子治病,费尽心力和财力。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蔡仪先生背着儿子出入各大医院,甚至远至上海。一九六六年,夫人在江西“四清”,上级又要求蔡仪先生到门头沟下农村。他只得把三个孩子,其中包括瘫痪的小豆,托付给老保姆。那年他六十岁。行前,他去东单买来猪骨髓,为小豆配制了丸药;熬夜到十二点,把孩子们棉裤开了线缝的地方一一缝好。一九六八年隆冬,小豆在瘫痪了十几年之后去世,活了十八个年头。师母乔象钟送别爱子时在东郊火葬场那一声“我的心呀”的惨叫,多少年叫人颤抖。蔡仪先生的失子之痛,可想而知。但是,当时还作为“黑帮”分子受管制的他,六十二岁,就已经白发苍苍,早上到东郊火葬场领了儿子的骨灰,抱着骨灰盒,转了几次公共汽车,送到西郊八宝山骨灰堂。天很冷。社会也很冷。失去爱子的蔡仪先生,心差不多冷透了,冻僵了。然而,那时他没流一滴眼泪。他知道他必须坚强。再大的灾难他也要挺住。因为他还有夫人和两个女儿需要安慰、照料。人家还强迫他去接受审查。他抱着儿子的骨灰从古城的东郊颠簸到古城的西郊,吞咽着悲伤。中午回到家,充满抚慰地对夫人说:“不要难过了。这是最好的结束,没有痛苦,他舒舒服服地过了十八年。”那天下午,他又“上班”--接受管制去了。
最值得提及的,是他对纯真爱情的忠贞和对夫人乔象钟的一片深情。青年蔡仪写了许多情诗,发表在当年的《华北日报》副刊和《沉钟》上。而诗,最能见真性情。有一束诗叫《杜鹃草》,其中一首题为《是谁?》:
是谁播下这可怜的种子,
叫我来殷勤地守护不止?
这园地常吹着冷酷的北风,
终年地凝着凄冷的薄冰。
我每次拨开土壤去探查,
定看见里面寂寞的毒蛇,
阴郁的蜈蚣,悲哀的蚯蚓子,
冷白的眼光在四周窥伺。
它们是鬼怪一样地忽隐忽现,
驱逐吗?一天也要驱逐千遍!
疲倦了,厌恶了,这无聊的工作,
何时她才到呢?我等着等着。
她吹着一支玛瑙的红箫,
叫空气发酵酿成着春醪,
游遍了天涯,山隈里,海滨,
可从没有敲敲我心的园门。
“这园里,姑娘,曾播了种子,
只要你春光的眼睛一视,
仅仅的一视,它便可以发芽,
抽叶、成条,开着美丽的鲜花。”
我低低地在她身后细语,
不顾地她飘然向前走去。
疲倦了,厌恶了,一切是已经绝望;
只得让毒蛇蜈蚣去将他埋葬。
二十一年三月,蔡仪
一九八五年八月,蔡仪先生把这首诗重抄一遍,赠送夫人,记曰:
“这诗是一九三二年三月写的,即发表于当时的《沉钟》上。一九八五年八月,我抄下它送给我的爱妻象钟,我预言的吹箫人,在十多年之后,让春光的眼睛照着了这种子,使它发芽、抽叶、成条,开了丰硕美丽的鲜花,现正红艳艳地开着呢!”蔡仪先生所说的“现在”,他七十九岁、夫人六十四岁。这是七十九岁高龄的蔡仪先生对六十四岁的夫人又一次爱情表白,情感浓得化都化不开。这对老夫妻的“丰硕美丽”的爱情“鲜花”,永远是那么“红艳艳地开着”!青春常在,爱情常在,至死不逾。
我们的“纸条”导师
蔡仪先生对自己的学生也充满深厚情谊。他循循善诱,尽心尽力,而且有自己独特的指导方法。
大约是一九七八年底,蔡仪先生创办了一个刊物《美学论从》,点名叫我写一篇文章。他始终关心着我这个“开门弟子”,大概想实际考察一下我的能力,看是不是做学问的料。我花了三个月,用上了我自上大学接触文学问题以来所有的积蓄--也包括我第一次接触文艺理论着作,阅读蔡仪先生《现实主义艺术论》时的体会,翻阅、研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参考文献,写成《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三万六千言,战战兢兢送到蔡仪先生手中,心提到嗓子眼儿上。过了几天,蔡仪先生把我找去,说对文章很满意,但也有些意见,我的心才放下来。
我回头看蔡仪先生审阅过的稿子。本来五百字一页的稿纸,整整七十二页,已经够厚的了;现在又增加了许多厚度。因为蔡仪先生加了许多纸条进去,贴在我稿纸的边沿上。有时同一页纸,上下和两边贴的都有。有的纸条几句话,甚至少到几个字,如“这段写得不错,就应该这样分析”。有的纸条写得较长,数百字。我记得最长的一段差不多一页纸,主要是谈“审美”这个词的使用问题。蔡仪先生对我这篇文章的最大意见,是滥用“审美”这个概念。他说,美是客观的,美感是对美的认识,是主观的。美就是美,美感就是美感。客观就是客观,主观就是主观,这两个东西不能混淆。“审美”这个词,就把客观和主观混在一起了,煮成一锅粥,怎能说得清楚?他就这个问题反复作了阐释,也讲了哲学上的主客概念和关系问题。就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具体问题而言,我虽然并不完全同意蔡仪先生的意见,但是我很为他的谆谆教诲和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
我算了一下,蔡仪先生贴在那篇稿子上的纸条,总计有三千多字。
蔡仪先生习惯于用贴纸条的方法指导自己的学生写作。对我的师弟们,也多如此。
我猜想,贴纸条,表现了蔡仪先生的为人行事的作风和态度。一是,蔡仪先生为人谦和,不愿在别人(即使是学生)稿子上乱划,也不愿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贴纸条,不损伤原稿,不同意,可以揭去;蔡仪先生自己发现哪条不合适,也可以撕掉重写、重贴。二是,一篇长稿子,洋洋万言甚至数万言,阅读过程中就有许多想法,需随时把意见写下来,用纸条很方便。三是,蔡仪先生爱整洁。他要随时保持纸面干净。用笔(无论钢笔、铅笔、毛笔)涂划,总不干净。顺便说说,蔡仪先生之整洁,我深有印象。一次在所里开会,热了,脱掉外面的中山服只穿衬衣。脱下来的那件蓝色中山服,旧了,但很干净。一般人衣服脱下,随便一扔,得了。但蔡仪先生不。他把它在椅子上细心叠好,齐齐整整,放在一旁,好像刚从洗衣店取回来一样。
话再说回来。对我的第二篇长文章--关于李渔美学思想的,后来扩展为一本书《论李渔的戏剧美学》,蔡仪先生的意见除了少量写在稿纸上之外,也是大量用贴纸条的方法指导的。在我的《论李渔的戏剧美学》的后记中,曾记述了当时我还称为“蔡仪同志”的蔡仪先生指导我的情况:“……他(蔡仪先生)看后对每一段都提了具体意见,有的写在稿纸上,有的写在纸条上而后又贴在稿纸上,最后,还用了三张纸写了总的意见,从文章的整体结构到一些具体问题,以商量的口气提出他的看法,简直像一个母亲教孩子学步那样。而过了两天,蔡仪同志又托人带了一封短信给我,说是还有点想法忘了谈,即认为:本来我的文章写得还生动,而这一次,却显得拘谨些,各部分的写法也显得雷同,希望我不必缩手缩脚,要放开来写。”
当然,这位“纸条”导师绝不限于写纸条。他对学生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全面的,从做人到做学问。譬如,他要学生一定要认真读书,读原着,读经典,读马克思主义,读中外名着。一九六五年底,我从安徽寿县四清和劳动锻炼回来,一见蔡仪先生,他马上就塞给我一个长长的书单,--这是我做研究生首先必须完成的阅读任务。我按照蔡仪先生开的书单认认真真读了半年,可惜没有读完,因文革爆发而被打断。再譬如,拿引文这件事来说,他一再强调,引用别人的话一定要注明详细出处,而且一定要引全,不能引半句话之后就批评人家如何如何。引用经典着作尤其如此。他说,这是做学问的起码规矩,也是起码的严肃认真的态度。
少见的工作狂人
蔡仪先生是一个工作起来不要命、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用的“工作狂人”,这劲头儿,同何其芳同志有点儿相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初几年,我参加蔡仪先生主编的《美学原理提纲》以及后来的《美学原理》的写作,并且围绕这项工作开了几次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一个共同感觉:凡是蔡仪先生主持的学术研讨会,“劳动强度”太大,常常让你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一天会下来,年轻人都觉得很疲劳,晚饭后出去散散步,晚上的时间各房间串串,谈天说地,有的还唱唱跳跳,放松放松。但是,几次会上,晚上青年人休息的时候,人们每每看到只有一个房间里有人工作,那就是蔡仪先生。一九八四年在北京西郊召开研讨会时,有一天晚上快十点半了,外地来参加会的一位同志非要找蔡仪先生,我犹豫了一下--蔡仪先生休息了吧?但看到这位同志那么殷切,还是领他去了。当我轻轻推开蔡仪先生房门时,见房间暗暗的,只有桌上的台灯亮着。蔡仪先生独自坐在写字台前的台灯下面,伏案阅读,并写着什么。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七十八岁高龄了。这个形象使我久久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