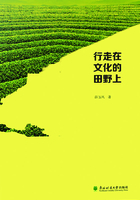我把挎包挎在肩头,转身欲走,这时候,有一种来自肩头的重量,不是固体的重量,也不是液体的重量,却迫使我朝他鞠了一躬,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回去了。回到四川,回到内江师专。唉唉,我离开黄维寓所以后是沿着马路对面的永定河走的呀,虽说方向朝西,目标也是106路电车的永定门站呀,永定,永定,可走进我的寝室,伏在案头,心神竟是这样不定!是黄维那滴泪水,化成了蒸腾在沱江之滨的晨雾,让我抬起头来就可以看见梦的残丝么?是黄维那颗黑痣,加重了降落在远山之下的暮色,让我推开窗户就可以看见魂的星光么?不知怎的。我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尤其是在我铺开的500字的稿纸上,哪怕是他的一根白发,也可以覆盖掉方方正正的全部格子!
我决定动笔。我决心写他。据说写作之前,要的就是这种动荡的情绪。可是,3天过去了,我没有能够落下一个字来;我能够落下来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了解他么?我理解他么?他之存在,他之存在的形态,我拿得出必须拿出的依据么?
倒是大自然孕育着社会的奥妙与秘密。窗外水的流动、帆的运行,是通过山之不动得以呈现的。那么我的参照物是谁?是我的舅父?不是。他作为国民党战犯,虽然曾经和黄维关押在一起,但不是一起被释放的。他获赦是最先的一批,而黄维是最后的一批,其间整整相距15年,相距了一个婴儿成长为少年的全部时间……最后一批获赦人员当中,我想起了文强。他是我在离开北京那天见到的。
作为一种依据的补充,我需要说明的是,当年他曾以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总参谋长之身,与黄维一起被俘于淮海战役。那天他坐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的沙发上,红光满面地接受了我的采访。“您老高寿几何呀?”我问。“我是1975年3月19日出生的,”他笑眯眯地说,“今年还未满5岁呢!”我也笑了,虽然笑得有些苦涩,因为我在理解到了文强的心情的同时,蓦地想起了黄维……这就是说,倘若我的参照物是黄维,那么文强便是欢腾的水;倘若我的参照物是文强,那么黄维便是光秃秃的山。而把这光秃秃的生命和那未满5岁的年龄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真要感激造物的神明,把这个世界安排得如此合情合理、应有尽有了!
欠缺的是我用来写黄维的文字,这正如同他秃光腮部的胡须,我也许找得到稀稀疏疏的茬儿,但是我不忍心拔下来,那样会带下血、连下肉。他还未满5岁,那些稀疏的胡须看上去虽不是绒绒的、软软的、淡黄淡黄的,但是它是树的根,水的源,山的魂,只要树长出叶子,水变成河流,山成了峰颠,他就可以发现一个属于他的世界。太阳是属于他的,月亮是属于他的。正因为都是属于他的,也许他才会更加冷峻、更加矜持地宣称:太阳也有黑点,月亮也有泪滴……可是眼下,我还是写了他。在我那页被窗外的阳光和月光映照得雪白透亮的稿纸上,不能没有黑点与泪滴。写他,当然是写他的过去。那时候,他不仅没有生命,还欠着别人的生命,所以与现在光秃秃的腮部相反,他蓄着浓黑的长长的胡须,用以牢牢系住奈何桥的桥墩。他想死,可是共产党要他活,这就是发生在战犯管理所里的死与活之间的斗争。既然这场斗争的经过我已从我舅父、文强那里获悉,那么要写黄维,索性就从他的胡须写起罢。
——黄维的须发又长又黑。医书云:“发是血之余。”黄维不能不为他那心脏之外的躯壳——保卫灵魂的碉堡——的强大的抗力,常常发出掩蔽在胡须里的微笑。黄维曾像农民关注禾苗一样关注着自己的胡须的生长,进入战犯管理所以后,他的一切都像他那颗黑痣那样固定,唯有浓黑的胡须越长越多。
——黄维的黑痣,倒没有惹出什么麻烦,可是他的胡须,已引起他人的注意和警惕。宋希濂分析说,开始他仅以为胡须意味颓唐,现在看来情况比预料的严重10倍;胡须是连结国民党的纽带,是对抗共产党改造的长矛上的红缨。
辛亥革命之所以要剪掉辫子,就在于去除旧时代的赘疣,因此宋希濂认为,国民党战犯在脱胎换骨之前,必须先把皮肉打扫干净……有关黄维的文字,我远远不止写下这些,也许开始就写胡须的缘故,等我完成作品初稿以后,我发现我用蓝墨水写下的稿纸,居然要比别人用炭素墨水写下的稿纸还黑!黑,在人们的眼里,并不是好颜色,尤其是在红颜色已经被传统心理上升到了庄严的地位的时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我下一步必须接受的挑战是:有关黄维的文字,统统让他过目。
万水千山之外,过目的方式自然是这样进行的:我把稿子邮寄给他,挂号寄,他不会收不到;收到的时间早几天迟几天倒无所谓,反正是在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里。春天里面,永定河畔的垂柳绿映长堤,这是可以想见的;西三楼前的阳台霞染窗纱,这是可以想见的;202号房间客房里,黄维坐在他那把垫有线毯的凉椅上,拆阅着我的稿子。不待看完,他脸色一沉,甚至恶吼一声,这是可以想见的;他离开凉椅,双手剪背,来回踱步,起初快,尔后慢,最终伫立在阳台正中。垂柳摇摇曳曳地解开了他额前的眉结,窗纱飘飘逸逸地松开了他身后的拳头,于是乎,他眼睛一闭,两手合十,宽大为怀,普渡众生……这也不是不可以想见的呵!
然而,我绝对没有想到,我竟是用我那个帆布挎包,装着我的稿子,连同我的牙刷牙膏洗脸毛巾,以及我的幸运和我那莫名的欢愉,乘坐十次特别快车再度北上,然后顺着东流的永定河水,疾行200米,重登西三楼,然后双手取出稿子,双手捧送到黄维的眼底——他躺在凉椅上看。春寒料峭,那垫在凉椅上的线毯却早早地被拆除了,阳台的衣杆上不见晾晒,想必已被塞进柜子里去了。他看得这样认真,身体一动不动,凉椅一响不响,哦哦,他已经把有关他的页码翻过去了,身体还是一动不动,凉椅还是一响不响,唉唉,莫非他就是那床陈旧的线毯的化身,被塞进这间柜子似的客房里来了!而我成了什么?我成了那把凉椅,只有我才看见了我的心跳,听见了来自我的骨骼里的“吱吱”的呻吟。
“黄伯伯,我在纸头上骂你了……”“骂我?你没有骂我。”黄维从一种漠然的情态中回过神,反而朝我笑了笑,“你写的事情是真的。真的,就不叫骂,就算骂了,也是活该骂的……”
黄维难得的笑容倏然消失了,就在那冷漠的神色重新浮现的一瞬间,他突然从凉椅上坐立起来,左手拿着我的稿子,右手指着一段文字,迟迟疑疑地问:“你写的这件事情,也是真的么?”
我从他写字台前的座位上弯下腰,侧过面,顺着他那开始颤抖的指头看去。这段文字是写我舅父的。舅父洛阳战役被俘以后,关押在石家庄附近的井陉战俘营。战俘营里,他碰见了一个俘前担任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副司令官的江苏溧阳老乡。老乡表现很好,关了几个月便光荣参加解放军,调华北军政大学工作。临行之夜,夜深人静的时候,老乡悄悄把舅父唤醒,把自己几件衣物送给他,并要他也积极要求进步,争取早日出狱。此等时刻,舅父凝视着窗前明月,对老乡只说了一句话:“你若有机会回溧阳,请代我看一眼我的老娘,若身上还有零钱,拜托你给她买几块饼干……”
此事是舅父亲口告诉我的,我照实写来,不会有假。于是,顾不得黄维指头的颤抖,以及那双腿的痉挛,那腰身的摇晃,那胸膛的起伏,那脸颊的抽搐,那喉结的滑动……我朝他点了点头。
“我相信,我相信呵……”黄维的声音是从牙缝里出来的,却是沙哑的而不是尖利的,仿佛气流刚刚进入口腔就立即中断了,而有一股神经,一股牵动全身的力,却使他突然睁大眼睛,射出一束烂红的火苗之后,又突然紧紧地闭上了,闭上了……剩下的唯一的动作是靠他的右手来完成的。右手临近右眼了,是去为关闭上了的大门插闩的吧?那么为什么手心朝上,仿佛托着一个水碗?哦哦,手心已经贴在眼角上了,眼角旁的黑痣也就包在手心里了,那么开始慢慢揉罢,把湿的揉干,把干的揉湿。究竟泪滴是黑痣的溶化,还是黑痣是泪滴的凝固?今天非要把它们揉出一个结果来!
我这样看着,这样想着,看着黄维的手心,想着黄维的内心,当然,为了一种真正的了解和理解,我等待着他自己的表白。
他说了,虽然失之风马牛,然而他是停止了全部动作之后使用着满腹心力说出来的:
“你不是在上大学吗?又来干什么!”
……
-3-
现在,我需要从物体的含义上去区别固体与液体。
惊愕之余,我在心里笑了,他手里还拿着我的稿子,却问我是干什么来的。
而且如此大声武气,这般如梦方醒。
至于这个问题的细节,本来我一进门就想告诉他,非常想告诉他,结果由于他接过稿子便躺了下去的缘故,我现在只好慢慢退回到他对面的沙发上去,补叙一番。
我是从写完这部稿子说起的。那时候,我自然在四川,在内江师专。写完稿子以后的事情,通常说来,就是在众多的刊物编辑部或者出版社当中,找准一家,然后将稿子直接投寄出去。我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写的是发生在战犯管理所的真人真事。常识告诉我,这样的作品需要审核,需要主管部门的审核,所以我虽然也将稿子投寄出去了,邮件的地址却不是哪家编辑部,而是只此一家的公安部。
这自然不是投稿,可是我比任何一个投稿者都更焦急地等待着对方的复函。道理是简单的投稿者若是收到一家编辑部的退稿,还可以将稿子寄去另一家编辑部碰碰运气,而我呢?我没有余地,没有退路,只要公安部摇一摇头,我的几盆几十盆心血顷刻之间就会付之东流——沱江畔,那漫长的迷茫的沙滩上面,我手搭凉棚呵,翘首以望呵!编辑部处理稿子的期限是3个月,公安部处理稿子的期限又是几个月呢?且慢,且慢,公安部是处理公文的地方吧,我的稿子连“私文”也算不上呀!
奇迹发生了。仅仅15天!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收到了公安部所属的一个单位的通知,通知要我立即动身去北京改稿。就是这件事情么?哦,不止,远远不止,这份通知的本身又是一个关于速度的信息。关于沱江的流动的速度,关于沙滩的运转的速度,关于春天的到来的速度……比起这些速度来,我乘坐的特别快车显然是太慢了。好在我以待分配毕业生的身份来到北京的第二天,公安部3位副部长在他们办公大楼的客厅里接见了我。我当时的心跳却是太快了。这一快一慢,有效地抵消了一种反差,让我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和宁谧。若不是这样,即令我不会忘掉永定门,恐怕到了那里还会忘掉东西南北哩!
我端端正正地坐在黄维面前,讲了以上内容的话,算是回答了他提出来的问题。诚然,如同他的问题的提出一样,我的话里也带着自己的情绪。如果说他与我的反差是冷与热,那么我的目的正是抵消它。
抵消的结果,出现在这间客房里的温度是多少,我不知道。挂在门侧墙壁上的那支室内温度计距我太远,我看不真切。我看得真切的是黄维的脸。黄维的脸是测量他的体温的温度计,由此我知道,出现在他内心的温度现在是摄氏36度左右,正常。
“你说的那几位副部长,我都认识……”黄维的声音也偏低(他总是这样表里如一),“我想,问题不在他们都看你写的文章,问题在于你写的文章并不是只给他们几个人看的……你懂得我这句话的意思吗?”
我摇摇头。其实我听懂了一些。“他们了解情况……我说的是有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黄维显得有些急躁,声音因此而有所升高,“这些人看了你的文章,看到我们过去的样子,会拿来开心,拿来取乐的!比如,你舅父托人给老母亲捎几块饼干,那本是辛酸的事情,可是,这些人会觉得辛酸么?不会的,不会的,只会让他们在酒醉饭饱之余,多打几个饱嗝,多打几个哈哈……你说,你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偏偏要做这种事情呢?”
“黄伯伯,”他的话我完全听懂了,我需要立即回答他,“如果我写舅父只去写这一件事情,那是没有意思的,甚至是无聊的。但是——在黄伯伯没有看完稿子之前,我想说明一下——我写的是包括舅父和黄伯伯在内的一大批国民党战犯监狱生活的全过程。您老不是说有很多人不了解情况么?我的目的正是让他们了解情况,了解你们。至于了解以后能不能理解,有什么感觉,那就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我不知道我的话是否有一点儿说服力,反正说话说到这里,我发现黄维的嘴角在嚅动,在微微上翘!沉默,默默无言,这是不奇怪的,任何一种转变都需要安静的时间。可是,在这个时间里,为什么他的鼻子不安静呢?唉,唉,“哼”的一声,竟把他的微笑变成了冷笑,变成了讪笑,变成了令我乍暖还寒的连珠炮:
“仁者见仁,能够见到什么仁?智者见智,能够见到什么智?仁智这些东西,只能够和什么人连在一起?你学的是中文,大概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不知道开宗明义就有这么一句话: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我过去是将,是将军,你说见仁也罢,见智也罢,见什么都行。可是现在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什么?你不会不知道‘成王败寇’这4个字吧!”
我知道这4个字,但是我不知道这4个字会像一枚燃烧弹爆炸以后的四面火光,把我的惊诧、我的怔愣、我的恐惧、我的绝望,全部暴露在对方的视野之中。
黄维显然是看见了我的窘态才站起来的。他离开凉椅走近沙发,一手把沉甸甸的稿子递还给我,一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头:
“既然公安部的领导人支持你写,你就写去吧。只是请你不要写我。我的经历不过是一个旧军人的普通经历,监狱生活也不过是一个战犯的一般生活,加之我与世为忤,饱经忧患,实在不值得为他人道也……古话说,献拙不如藏拙,就请你遂我藏拙之愿罢……”
我接过稿子,一句话没说,或者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慢慢掉头走了。走出房门的时候,我回首瞥了黄维一眼。他依然站在那里。因为老太太不在家的缘故,他显得有些孤独。而我的目光却是告别性的,如果不是永别性的话。因为我相信,至少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我不会再看到他了……我开始了以另外的老人为对象的采访。去年来北京,时间仓促,行色匆匆,未能一一走到。走到的也形同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没有能够深谈得上。现在,我需要把工作的战线全面铺开来,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占领。如前所叙,我是从黄维的阵地上败退下来的,虽然不能说阵地与阵地之间沟壑相通,但是一次占领总是另一次占领的前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等待着一块石头的出现,为了确保石头棱角的锋利,我希望“他山”之他的脑袋,曾经是一块花岗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