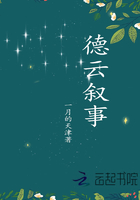去岁暮春,我为《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撰写书评(载2013年3月3日《上海书评》),文末表示:“据笔者所知,周作人晚年致曹聚仁、高伯雨、郑子瑜等也属于‘一心倾向周作人’者的大量信札依然存世,期待也能早日整理出版。”没想到时隔仅仅一年,周作人致郑子瑜的84通书札就惊现北京匡时2014春季拍卖会。
郑子瑜(1916—2008)是福建漳州人,为清代诗人郑开禧后裔,1939年南渡北婆罗洲。他自幼喜爱文史,21岁就主编《九流》文史月刊,后倾情于散文创作。1954年移居新加坡后曾主编《南洋学报》,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美国阿里森那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校研究或执教。他长期致力于周氏兄弟旧体诗、郁达夫旧体诗、黄遵宪与日本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尤以对古汉语修辞的研究为海内外学界所推重,所著《中国修辞学史稿》为世界第一部国别修辞学全史。
在与周作人通信之前,郑子瑜就与郁达夫、丰子恺等中国现代文学大家有所交往,本次同时付拍的丰子恺1948年至1950年间致郑子瑜的9通书札就是一个明证。他与周作人通信始于大陆“反右”运动告一段落后的1957年8月26日,终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前夕的1966年5月11日。这批周作人致郑子瑜书札,存有原件也即此次付拍者,总共84通,并附吴小如致郑子瑜、谢国桢致周作人和周艾文致周作人信札各1通,又周作人作《〈郑子瑜选集〉序》手稿等。
然而,这还不是周作人致郑子瑜书札的全部。这就要说到我与郑子瑜的关系了。1980年代初,因研究郁达夫,我与郁达夫研究史上第一位编订《郁达夫诗词抄》的郑子瑜取得联系。以后不断向他请益,他也为《中国修辞学史稿》出版事委托我与上海教育出版社多次交涉。而我们之间第一次成功的合作是,由郑子瑜保存的周作人《知堂杂诗抄》手稿经我略作增补后推荐给钟叔河主持的岳麓书社出版,时在1987年1月。郑子瑜在为《知堂杂诗抄》所作的《跋》中追忆了与周作人的交往始末,以及他谋求《知堂杂诗抄》出版的简要过程,笔者因此得知他珍藏着周作人的大批信札。当时因他正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客座,直至他返回新加坡,才于1993年2月寄赠我周作人致其书札影印件一套。二十多年过去了,这套影印件连同邮寄大信封均保存完好。
有意思的是,郑子瑜惠寄我的周作人书札影印件与此次付拍的周作人书札颇有出入。首先,郑子瑜是细心人,已对周作人手札按写信时间先后作了编号,此次付拍的84通书札原件最后一通和我收到的影印本最后一通右上角注明的编号均为95,可知周作人寄给郑子瑜的书札前后总共95通,这个数字应是确数。其次,此次付拍的周作人书札原件为84通,我收到的影印本则有86通。经仔细核对,有原件而无影印本的书札为4通,无原件而有影印本的书札为6通,有编号而原件和影印本均无的书札则为5通,这5通恐怕真的是不明下落了。第三,影印本所有的一些附录,如周作人1961年7月18日致日本实藤惠秀函抄录稿影印件等,也为书札原件所缺。最后,书札原件除了编号,还加注写信年份;影印本除了编号和加注写信年份外,更注明每通信寄往新加坡还是东京,还注明已缺了哪些书札,如编号18的信上注明“(17缺)”等。令我特别感动的是,郑子瑜担心我无法辨认信中的某些字、词和内容,还在不少信上加注说明。
因此,我探讨这批周作人致郑子瑜书札的学术价值,以此次付拍之84通原件为主,以我收藏之郑子瑜惠寄影印件为辅,以求更为客观和全面。这84通书札原件均为毛笔书写,或端正或随意,可充分领略周作人独具一格的书艺自不在话下。而信中与郑子瑜互通音问、切磋学术、赠送资料和闲话家常,又可从一个侧面窥见周作人1957至1966年间的生活、写作和心境,也毫无疑义。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在信中不断与郑子瑜讨论《知堂杂诗抄》的编选,这批书札呈现了一条较为清晰的《知堂杂诗抄》成书轨迹,从而大大有助于我们对《知堂杂诗抄》的研究。
据郑子瑜在《〈知堂杂诗抄〉跋》中回忆:“一九五八年一月我曾写信给周氏,问他可否将生平所作的旧诗寄示,或者可以代为设法出版。”果然,周作人1958年1月23日编号5信中说:“一月六日手书敬悉。鄙人自解放后未曾作诗,前在南京狱中曾少有所作,(有《往昔》五古十韵三十首。《儿童杂事诗》七绝七十二首,稍成片段。)俟将来抄出。再行呈教,或谋出板耳。大作拜读,属和则目下未能,俟后有兴致时或当勉力为之。”这是编辑出版《知堂杂诗抄》的初议。同年2月16日编号6信中又说:“《往昔》等诗当觅人抄写,但如人难觅得,(抄写不难,校对为难,有时较自写为烦。)则拟觅闲自抄,但病后字不成字,殊为难看耳。”2月24日编号7信中又说:“正在抄录拙诗,(因杂乱不能找人代抄,且抄了需校,亦大费事。)俟竣事后寄奉。诗文本不值钱,尤不便自行索价,俟后看了时值估价,鄙人决不计较也,但以得借此发表为幸耳。”到了3月14日,周作人在编号8信中告诉郑子瑜:“拙诗集二册另封挂号寄上,乞察收。只要能付印成书,便已满足,其余请由先生酌定之可矣。”由此可见,周作人出版旧诗集一事出于郑子瑜的提议,同时也得到了周作人的认可,他不顾病后体弱,亲自抄录诗稿寄郑,郑重拜托,并表示只要能付印成书,可以不计报酬。更重要的是,按周作人最初的设想,《知堂杂诗抄》只收入老虎桥时期所作的《往昔》和《儿童杂事诗》两组诗。
周作人既已交付郑子瑜旧体诗集初稿,《知堂杂诗抄》第一阶段工作即告一段落,但后续之事仍然繁多。1958年4月15日编号9信整通仍都在讨论诗集出版事,转录如下:
手书敬悉。拙诗拟分作两册,亦无不可,唯内容不显得贫弱否?杂诗旧有题记(代跋)今抄呈。嘱写新序文,恨无话可说,一篇或尚可,两篇或为难矣。容考虑再奉答。“苦茶庵打油诗”已印行,唯该书未发行而书店关门,将来似附录杂诗(在题记之后),请斟酌。
信中所说“杂诗旧有题记(代跋)今抄呈”,当指“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日,知堂自记”之《杂诗题记》,后收入《知堂杂诗抄》。“两篇或为难矣”,当指郑子瑜希望周作人为《往昔》和《儿童杂事诗》两组诗各写一篇新序。而《苦茶庵打油诗》“已印行”,当指这组打油诗已编入《立春以前》,但《立春以前》已于1945年8月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何以“该书未发行而书店关门”?想必是周作人记忆有误。不过,他明确表示,非老虎桥时期所作的《苦茶庵打油诗》可以“附录”《知堂杂诗抄》。
仅仅过了两天,周作人在1958年4月17日编号10信中便说:“拙诗自序写了一篇寄上,杂诗亦似作为一册发表为佳。一切统俟尊裁,弟别无主张也。”这篇自序未见收入《知堂杂诗抄》,想必后来又写了新序而弃而不用。周作人毕竟是讲究礼数之士,一方面他再次对郑子瑜拟将《杂诗抄》分成二册印行不予首肯,另一方面又表示“一切统俟尊裁”。四十天之后,他在5月27日编号11的信中对《杂诗抄》的编选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立春以前”便以奉赠,不劳寄还。“苦雨斋打油诗”虽非老虎桥所作,但说明作“附录”登在里边,似也不妨事。儿童杂事诗尊意单行为佳,可以照办。今将原作序抄呈,并附说明,因前在亦报登过,且有丰子恺画,不说明似不妥当。南洋商报似最好选登一部分,因原本有些也乏味也。此事序文中难以叙入,故略之。儿童杂事诗如抽出,杂诗似分量太少,但注解太费事,增添题画诗亦不相宜,如何乞尊酌。序中“共有一百几十首”原系包括儿童杂事诗而言,可请酌改,或径删改为“六十首”可耳。
这通书札与上引4月15日编号9信同样重要,周作人还郑重地落款后钤上名印。他再次同意《知堂杂诗抄》扩容,收入非老虎桥时期所作的《苦茶庵打油诗》(信中误作“苦雨斋打油诗”)。并把载有《苦茶庵打油诗》的《立春以前》一书寄赠郑子瑜;也同意郑提议的《儿童杂事诗》单印并寄其原序,此篇原序已收入《杂诗抄》。对《杂诗抄》分为二册后另一册分量如太少如何解决,也提请郑子瑜注意及之。至于信中所说的“序中‘共有一百几十首’”云云,因此序已失,详情也就无从知晓。总之,《杂诗抄》初稿虽已成,此时还在不断地协商、调整和充实。
郑子瑜当时还通知周作人,拟将《儿童杂事诗》交新加坡《南洋商报》先行刊登,周作人也在此信中表示了态度,“最好选登一部分,因原本有些也乏味也”。在7月24日编号12的信中又对此事具体有所交代。此后一年余,周郑之间无通信。到了1959年10月25日,在编号14的信中,周作人对印行《知堂杂诗抄》旧事重提:“拙诗承蒙厚意斡旋。无甚感荷。至于出板条件则但求得印出,俾可以给人,省得钞录。稿酬在鄙人所不计较,但请代斡旋,只要说得过去就好了。”想必是时间过去一年多,郑子瑜在新加坡印行《知堂杂诗抄》的努力没有进展,周作人有点焦急了,再次表明“不计较”稿酬的态度。
一个月后,周作人旧体诗集的出版似乎有了转机。该年11月25日编号16信中,周作人通知郑子瑜:“顷得香港友人来信。云有新地出板社,拟将拙诗‘往昔’刊行。为此如尊处出板计划尚无头绪。请将拙诗全稿并跋寄去,合并为一册。为省稿件转寄的麻烦,请由尊处直接寄港,‘香港大道东循环日报馆朱省斋’收可也。”为答谢郑子瑜的前期努力,周作人特请郑子瑜为《知堂杂诗抄》作跋。1960年1月7日编号17的信中,周作人这样说:“承赠为敝集作跋,已收到矣。尊文中有过奖之处,因为略加修正。日内当寄给朱君。唯港之出板社能否接受,亦未能预定,一切且看朱省斋先生与出板社交涉如何耳。”2月1日编号18信中又说:“拙诗集朱君来信云已收到,由新地付印。大抵全是铅印,故无须原稿也。”同年1月28日,周作人为朱省斋拟印之诗集作了序,序中对郑、朱两位均表示了感谢,此序已以《前序》为题收入《知堂杂诗抄》。
接着周、郑之间的通信大致围绕为《郑子瑜选集》作序、吴小如辑《人境庐诗》出版、打听陈望道地址、周艾文与郁达夫旧体诗词的编集等事而展开,周作人在信中对郑子瑜欲联系的俞平伯和丰子恺均不无微词。直到1960年10月31日编号31的信中,周作人又提到《知堂杂诗抄》在港出版不容乐观:“至于拙诗,系在港友人携至彼地,云由新地出板社出板,其迟出缘因当别有在,唯据友人(不是朱省斋)来信说仍拟刊行,其日期则难以预知耳。”这位将周作人诗稿“携至彼地”即香港的友人当为曹聚仁。在同年12月25日编号32的信中,周作人就说得很清楚:“我的老虎桥杂诗则因为在香港出板不景气之故,亦恐一时没有希望。此书前与新地出板社接洽,已经说要,但现今该社的乡土半月刊亦已停顿。将来原稿索还后,仍当寄还先生。朱省斋君业已离循环日报,此事现托曹聚仁君代为接洽办理。”
不料事情又峰回路转。次年即1961年1月15日编号33信中,周作人告诉郑子瑜:“旧诗集据曹君说,拟另找出板处,颇有希望,故尚不便索还,只能再看机会。”然而,“颇有希望”,毕竟还是没有希望。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无从推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月后,《知堂杂诗抄》仍要退还郑子瑜,托其在新加坡重新谋求出版了,这有1961年2月14日编号34信为证。此信在此次付拍原件中并无踪影,故特别有必要转录如下:
关于拙诗集承关心甚感,兹有数事拟先商量:
一、拙集仍拟合并一册,因为此废物不值得出两册也。当先商之曹君,如港方无办法,则拟请仍照“杂诗”形式,包含“儿童诗”在内,唯插画可以略去。
二、如在新加坡出板,拟先一打听出板社是否有政治色彩,万一有什么关系,则于住在国内的人很有妨碍。此事想在谅解之中,特再说及。
三、赠书以代稿费,当然不成问题,唯个人赠送有限,尚有多数剩余,可否由出板社作价收回。如此虽不算稿费而仍在(有)若干现款汇下,对于国内的人甚有利益。……
周作人所提三项要求,条条在理,尤其强调出版社不能有“政治色彩”,可见其之小心谨慎。对这些要求,想必郑子瑜也均会同意。在同年3月15日编号35的信中,周作人又对前信作了两点极为重要的补充:
诗集承关注,甚感。有两点仍请考虑。一、名称用苦茶庵觉得不妥,因为那些杂诗不是在苦茶庵所写的,拟改用“知堂杂诗抄”。如此则稍赅括,儿童诗亦拟收在内(插画可省,因此系丰君板权),不然单行恐不易出板也。二、即酬书多余折钱之事,反正不要求多赠,谅可不成问题,因书多寄递不便,且鄙人也无需此数也。此二点祈考虑后示知为盼。题画诗记得前曾抄奉,今重加增补,比前次为多,又打油诗补遗亦同封寄呈,祈察入。上月照一相,以一纸奉赠,俾得见老病余生之本相耳。
正是在这通书札中,周作人首次确定旧诗集名“知堂杂诗抄”,而且坚持诗集包括《儿童杂事诗》在内,不分册,只出一集,同时增补了《苦茶庵打油诗补遗》和《题画五言绝句》两组诗,还寄去了可供插图用的近照。至此,《知堂杂诗抄》第二稿已具规模。
当然,周作人以后对《知堂杂诗抄》仍不断有所增补。1961年3月27日编号37信中说:“拙诗集出板办法,请斟酌决定。抄呈‘自寿’诗二纸,祈为编入或加在‘苦茶庵打油诗补遗’之后。印刷不必求精良,只求普通可备披览足矣。集中如须附照相,前此寄呈的一枚系现时所照,恐不适宜,别有当时(一九四九年春天)在上海所照的可以寄去。”奇怪的是,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七律二首)当时并未补入《杂诗抄》,现在《知堂杂诗抄》中所收的《自寿诗两章》是1987年1月岳麓书社初版时才补入的。而《杂诗抄》所刊用的照片也仍为“一九六一年摄于北京”的那枚。同年“四月初八日”编号38信中,周作人又寄给郑子瑜两张照片,“小张系在上海所照。距写诗时期不远,又一张则在家里,虽有庭院背景,却是晚了。送请尊酌办理”。但后来的《杂诗抄》均未采纳。
1961年4月20日,周作人应郑子瑜之请,新写了《〈知堂杂诗抄〉序》,此序手稿已制版置于《知堂杂诗抄》卷首。次日在致郑子瑜的编号39的信中,周作人说:“顷已写就杂诗集序,特附上,祈察收是荷。苦茶庵打油诗乞依原文编入,至补遗则只是诗而无文,似不会得有重出之处也。”信末他又添加了一句重要的话:“忠舍杂诗拟不收入,已于前函说及。”其实,周作人记错了,他并未把《忠舍杂诗》稿寄给郑子瑜。在1961年4月17日编号40信中,他就这样回答郑:“‘忠舍什诗’如前回的稿上原本没有,现在也不加添了。”在此信中,他又寄给郑子瑜诗一首“希为编入”,另有一首“望代为删去”,惜均已不可考。他又把一份“蔡孑民手稿”寄赠郑子瑜,“或者印入集中亦可”,那应该是蔡元培的和《五十自寿诗》手稿,但这个建议并未实现。信中还与郑子瑜讨论了《杂诗抄》选用哪首诗稿作为插图等具体问题。
郑子瑜当时是与新加坡世界书局接洽《知堂杂诗抄》出版事宜的,1961年5月11日编号42信中,周作人说:“嘱自写书名,附上一纸,乞察收,反正写不好,所以也不多写了。”可见当时已经进入了题写“知堂杂诗抄”书名的阶段,似乎进展颇为顺利,《知堂杂诗抄》出版有望了。
然而,好事必然多磨。出版社方面审稿以后,提出了新的要求。1961年5月29日编号43信中有如下的话:“诗集事承种种费心,不胜感谢。承询两样办法,鄙意以第二种为宜,因‘新诗’不成东西,且已发表过,只有甚(杂)诗算(值)得印出,可省抄写之烦,故仍拟用‘知堂杂诗抄’名义,但下署周作人著而已。所拟删去的系什么样的诗,统由编辑者处理,唯祈将其篇目开示为荷。”原来出版社一要增加新诗,改动书名,二要删去若干首诗,以至周作人不得不作如此表态。
不过,新诗当时未编入,删诗之事似也未具体进行,从后来出版的《知堂杂诗抄》所刊出的周作人自拟“目录”手迹看,除《忠舍杂诗》按其1961年4月17日信中意见不予收入外,其他各组诗作书中均保留了。尽管如此,《杂诗抄》出版事进展仍然缓慢,1961年6月13日编号44信中,周作人要求郑子瑜:“纸只用普通报纸好了,排印行款亦祈代定。一联一行,或照旧式接排,均无不可。唯末校,可否赐阅一次,倘有误字当航空奉复也。”其目的就是希望早日将《杂诗抄》印出。
十天之后,周作人在1961年6月23日编号45信中表示:“诗集赠书任凭书局给予多少,不成问题。诗除前此奉托之外,不拟再有增删,即请付印可也。诗稿附奉二纸,一系新书,似乎草草不工,又一纸系旧日所写,未知那个可用,希代为决定用之。至底稿则可不必见还,便留在尊处。”显而易见,对《知堂杂诗抄》的出版,周作人在此信中包括插图诗稿和出版后原稿如何处理等问题在内,再次作了具体而又明确的交代,言下之意,《知堂杂诗抄》已经定稿,他的工作到此已经全部结束,不再赘言。
遗憾的是,郑子瑜到底还是功亏一篑。此后一个多月里,周作人信中未再提及此事,直到同年8月10日编号48信中,才又说到《知堂杂诗抄》:“诗集既难出板,亦可无庸自费付印,因诗无此价值,若自印必然徒招损失也。惟先生的好意,则一样的深所感激。”出版社最后拒绝了《知堂杂诗抄》,郑子瑜因此而有自费印行之议,周作人才在信中表示反对。
紧接着,似乎又有了一丝希望。1961年8月26日编号49信开头就说:“得十四日手书,敬悉。诗集仍俟周君(当指世界书局负责人周星衢——笔者注)回来再说,如此甚好。”但从此仍毫无下文。其间还有一个插曲,当周作人告诉郑子瑜,曹聚仁拟在香港印行其“文选”,郑又有“文选”可附录《杂诗抄》之建议,1962年5月28日编号58信中,周作人说:“文选事系曹聚仁君发起主持,鄙人未知其详,尊意杂诗亦可附在末尾,唯窃以为最好还是单行,如能出板什么条件都没有,一如前此所说的那样。”尽管“什么条件都没有”,但《知堂杂诗抄》在新加坡单行出版就此彻底搁浅。
到了1962年6月27日,在编号60的信中,周作人再次反对郑子瑜自费印行《知堂杂诗抄》:“拙诗不能出板亦无妨,请勿自费刊行,非徒太耗费,亦实不值得也。”这是周作人对《知堂杂诗抄》出版与否的又一次表态。不久,郑子瑜就去了东京早稻田大学。1964年5月25日编号83的信中周作人不赞成郑子瑜拟在日本影印出版《知堂杂诗抄》,由于此信在此次付拍的书札原件中也无踪影,同样很有必要转录如下:
拙诗承蒙费心,甚为感荷。唯仍以排印为佳,不值得影印也。书名用老虎桥杂诗为宜,或附录前作,乞尊裁。儿童杂事诗印本(曹君已寄还给我)曾寄给在青海的友人,现去信索回,不日可到。
信中所说的“儿童杂事诗印本”当为《儿童杂事诗》1954年写本的香港影印本。可以想见,郑子瑜在日本的努力仍未成功,周作人在1964年7月12日编号86信中批评日本出版界时间接提到了一笔:“日本出板界只是生意经,全在投机,想正热心于《红岩》等时髦小说,对于落后如鄙人的东西加以留意者亦只是个别的人罢了。先生著作正是白费心思,故鄙人对于拙诗亦不甚汲汲求发表也。”
此后直到1966年5月11日编号95的最后一通信,周作人不断与郑子瑜讨论郑很感兴趣的另两个话题,即黄遵宪和《人境庐集外诗》种种、国内编集郁达夫旧体诗词种种,以及他自己晚年的重要作品《知堂回想录》(原题《药堂谈往》)种种,却再也未向郑子瑜提及《知堂杂诗抄》。但在他内心深处,一定为此事功败垂成而深以为憾吧?不仅如此,当郑子瑜流露拟研究他旧诗的想法时,周作人多次表示大可不必,如1963年5月22日编号71信中加以劝阻:“鄙意拙诗殊无研究之价值,如为此花这般力气,亦实是不值得也。”前辈风范,不能不令人钦服。
《知堂杂诗抄》是周作人晚年亲自编定,堪与《知堂回想录》称为双璧的重要作品。周作人虽然一再自嘲《知堂杂诗抄》是“废物”,“无此价值”,其实颇为看重这部旧诗集。从1958年1月23日编号5信中周作人答复郑子瑜的建议,到1964年7月12日编号86信中周作人最后一次提到这部诗稿,差不多五六年时间里,《知堂杂诗抄》虽然编成,谋求出版却一再受挫,其间的复杂,其间的曲折,真是一言难尽,也是我们以前所根本不知道的。与《知堂回想录》一样,周作人直至去世,也未见到《知堂杂诗抄》问世;与《知堂回想录》不同的是,《知堂杂诗抄》在周作人去世整整二十年之后方始与世人见面。这当然要归功于郑子瑜精心保存诗稿。而随着周作人致郑子瑜书札原件的“出土”,这位七十多岁老人为这部诗稿所花费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所遭受的种种尴尬和无奈,都在书札中几乎表露无遗。这批珍贵的书札在周作人作品出版史上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和非同一般的意义也因此得以彰显。
(原载2014年5月25日上海《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