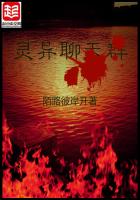我听了他们的话就想,这种茗战实在级别不高,要真是有高手在其中,打死他们都不愿意在这种鬼地方煮茶。种种迹象表明,这伙人肯定没有上等茶叶,更不太懂茶道,否则真是大大地浪费了珍贵的茶叶。
他们煮茶时,从水里看到一个人跑出来,吓得魂飞魄散,还以为是几十年前的死鬼出现了。有一个叫老潘的人发现了情况,于是招呼众人提高警惕,但那人从水里出来后就跑了。老潘觉得不放心,于是从大院里借了只狗下来,想要防鬼防怪。狗调皮惯了,一下来就把老潘的茶叶吞了,急得老潘想跳起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潘没了茶叶怎么煮茶,情急之下就把狗杀了,然后想将茶叶取出。
不巧的是,这时我们的两个工人发现了被堵住的窟窿,他们游到了池子里,却遇到了正在杀狗取茶的老潘。老潘杀狗杀得红了双眼,他以为水池里又跑出两个水鬼,没等两个工人喘口气,他就将工人们捅死在水里。发生了这些事情,煮茶的众人顾不上茶叶,纷纷逃跑,只有一个叫作廖富贵的人不肯离去。
廖富贵就是用风炉和鍑烧煮茶水的人,他看起来贼眉鼠眼,属于那种脸上写了坏蛋的人。廖富贵一直守在水牢的房间里,直到发现我们越走越近,他才崩溃地逃上地面,煽风点火地请众人打鬼。这群人地面上冷静后,操起家伙,你推我我推你地杀下来,双方对峙后才把误会解除,可惜两个工人白死了。
第一个跑掉的人肯定是小吴,但他既然生还了,应该回到工地报道,为什么又一声不吭地跑了?我和赵帅问这伙人,他们却反问我们,闹到最后谁也不知道小吴逃走的原因。我担心李师傅等急了,于是和赵帅商量先回工地,然后再把后事处理妥当。杀人的老潘意识到误杀后,他当场畏罪潜逃,别人想拦都拦不住。
当我们要离开时,廖富贵却挡住了去路,然后说要把我手里的牺杓物归原主。据廖富贵的一面之辞,牺杓是他的东西,茗战前被老潘借去了。老潘杀狗以后,想用牺杓挖出茶叶,意外之下在水里与两个工人打斗时,牺杓被撞到了探测洞那边的积水里。我很想问廖富贵打哪儿找来这么珍贵的玩意儿,看起来不像他这种人所有,但当着众人的面,廖富贵坚持说是祖传的东西。
事情搞清楚了,赵帅就催我把牺杓还给人家,然后离开了地下水牢。当晚,我在与工人们的交谈得知,小吴平时好赌,欠了很多赌债,再不还就要被黑社会做掉了。小吴掉下探测洞后,他可能发现了窟窿,于是借机逃跑,妄图赖掉欠债。我们之前没发现窟窿,估计是小吴搞的鬼,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窟窿还是被发现了,而且搭上了两个工人的性命。那晚小吴逃走后,谁也没有再见到他,或许他已经被放高利贷的黑社会弄死了。
这件事情对工程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后来仍把工程做完了,但引起了连环效应。赵帅老爸的生意因此受到重创,其他竞争对手趁机背后使坏,害得赵帅他爸积郁成疾,一病不起。赵帅老妈的身体也不好,她都自顾不暇了,还要看护老伴,可谓苦不堪言。
为了住院经费,赵帅家甚至卖掉了北京的房子,情况和我小时候经历的几乎一样。赵帅一直闷闷不乐,竟很久没再找女人,日子过得跟和尚没什么区别。赵帅认识很多有钱的公子哥,遇到困难后他曾去找过那些人,但他们躲都躲不及,哪还会伸援手。我不好意思再在赵帅家里蹭吃蹭喝,于是又住回松榆里的地下室,这一回我又遇到了一个贵人,只不过这个贵人比我还惨。
松榆里的地下室住的都是穷苦的北漂一族,自然不会有大富大贵的人涉足,我住进去以后几乎闭门不出。赵帅来看过我几次,尽管家境不同了,但他依旧衣冠楚楚,西装革履。其他住户看到赵帅,他们就不停地问我,是不是哪家有钱人的亲戚,能不能介绍几份好工作。凡事总有例外,有一个穿着妖艳的女人从不问赵帅是谁,反倒是经常来找我说话。这女人叫李秀珠,我一眼就看出她是小姐,她也没有否认。可我穷得叮当响,无利可图,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以我很好奇她为什么老是找我。
一天晚上,李秀珠又来敲我的门,她依旧不请自来,不请自进。我其实也有点想法,否则不可能让李秀珠进屋,无奈囊中羞涩,锅都揭不开了,因此找女人的想法很快被扼杀了。这么多天了,李秀珠总是问些有的没的,我都敷衍了事地回答,大家也慢慢熟悉了。进了屋后,李秀珠看了看我床头的几本书,问我是不是读过大学。
“是啊,怎么问这个问题?”我坐在床头,随手拿起一本书,刚好捡到残本茶经。
“这段时间经常打搅你,不好意思。”李秀珠今天不施粉黛、纯真质朴,搁在过去没准是个三八红旗手什么的,如今的社会太难混了。
“谈不上打搅,反正我也没事干。”我客气地说,心里却觉得很寂寞,挺想找个人聊聊天。
“我准备离开北京了,想请你帮个忙。”李秀珠有点害羞,她犹豫了一下子,然后说,“你能给我的孩子起个名字吗?”
“啊?你孩子?起名字?”我惊讶得连连发问。
李秀珠淡淡地笑了笑,她坦承自己是小姐,除了读初中的弟弟,她从小没接触过读书人,我是第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个。李秀珠已经攒了几万块,准备回家乡找个男人嫁了,所以临行前想找个读过大学的人给孩子先起好名字,将来也许能行好运,也读个大学。李秀珠可能看出我的心思,她斩钉截铁地说,将来要是有了孩子,什么都不让他干,穷死累死也要供他上大学,堂堂正正地做个人。
我没敢说读了大学不见得会有没出息,譬如我,还不是窝在地下室里挨日子,要饭都轮不到我。李秀珠没给我机会回答,她一股脑地倾诉,仿佛一肚子的话憋了很多年了,今天不说不痛快。李秀珠说自己是个坏女孩,但会努力做个好母亲,此时她浑身的野性居然透出一道圣洁的光芒。
在谈话中,我得知李秀珠小时候读书特聪明,但穷乡僻壤的,都认为送女儿读书没用,所以早早辍学了。李秀珠回家种了几天的地,挖地三尺,硬是刨不出吃饭的钱。于是,李秀珠远走他乡,到城里打工。以前在饭店里洗碗,一洗就是一天,腿都站不稳了。后来经朋友介绍,去做小姐,一开始她还不习惯,后来朋友劝她,说女人有什么,不就是两腿夹个宝吗,不拿来赚钱,给谁留着?
李秀珠原本不愿意,但笑贫不笑娼,家里的父亲等着钱看病,弟弟的学费还没着落。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李秀珠心想什么人什么命,两眼一闭,爱谁谁吧。卖身子的钱不干净,但钱又不咬人,攒够钱再回去嫁人,开个小卖部不再卖身子,只卖油盐酱醋。
我听后心里不是滋味,现在不能把李秀珠当成小姐了,谁想过小姐的背后也有故事。若干年后,李秀珠成为人母,她的儿女不会想到母亲曾有过这么一段往事。李秀珠说着说着就掉眼泪了,她让我别笑话她,再过几天她就要收手离京,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了。我叹了口气,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在中国一个亲戚都没有,还能去投靠谁,总不可能也去做“鸭子”吧。
“你这几天给我想两个名字吧,一男一女,不用考虑姓氏,就想想后面的。要是我回去嫁人了,那群没文化的人起的名字肯定难听得要死。”李秀珠擦干泪水,笑着说,“我明天请你吃饭吧,相识一场,就当是离别宴。”
“不用请客了,起个名字而已,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想想。”我保证道。
“您这么有文化的人,又认识有钱人,怎么会住在这里呢?”李秀珠忽然问道,“该不是犯了什么事,躲在这里吧?”
我涨红了脸,辩解道:“这倒不是,只不过……一分钱能难倒一个英雄,你也能体会吧?”
李秀珠扑哧一笑,说道:“跟你闹着玩呢,读书人果然正正经经的,能犯什么事啊,不过你要是真缺钱,我可以先给你垫上。”
我听了马上拒绝,就算是饿死,也不能用李秀珠的钱,倒不是嫌钱不干净,而是那钱是她离开火坑的资本,我拿了那些钱,肯定会遭天谴的。李秀珠倒很大方,她完全不担心我拿钱就跑得无影无踪,对读书人的信任程度简直不可思议,没有相同经历的人是很难体会的。李秀珠看我不肯用钱,当场就佩服读书人的骨气,更肯定她没看错人。
我一想到当初还对李秀珠有想法,马上觉得汗颜,自己真他妈不是人。可能是被李秀珠打动了,我也把自己的故事说了出来,就连怎么回国的原因也说了,要知道这事我都没跟赵帅提过。李秀珠听得一惊一乍,并说她果然没看走眼,面前的这个男人竟真的大有来历。我尴尬地笑了笑,英雄不提当年勇,这些事情说出来只会显得丢人,根本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话末,我问李秀珠是哪里人,她想也没想,就说自己来自云南的勐海县,也就是旧称的佛海。
我大吃一惊,勐海是祖父曾待过的地方,想不到今日竟能遇到勐海人。李秀珠只知我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原因,但不知道祖父发迹的历史,她还在侃侃而谈,说自己是僾伲人。在僾伲人是哈尼族的一个支系,古称乌蛮、和蛮、窝泥等等。根据哈尼族口碑传说,他们的先民原住于北方一条江边的“努美阿玛”平原,在秦汉之际迁入云南。
关于这些事情,李秀珠是从村里的教书先生那儿听来的,所以等不及地想显摆一番,吓一吓眼前的读书人。听到勐海这个地名,我哪里还关心这些有的没的,当下就忙问李秀珠,勐海是不是曾有一个英国人留下的宅子,且已经荒废很多年了。
李秀珠愣了一下子,茫然地看着,然后想了想,说勐海的确有一座英国殖民者留下来的大宅子,不过那宅子很不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