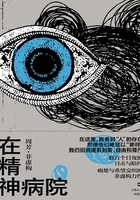如果把牲口分个三六九等的话,那么马就是一等了,你看它傲视群雄气度不凡的样子,不就是一人之下万万牲口之上的架势吗?甚至于有时候它连人都不放在眼里,简直自己就要君临天下了,当然这样会惹人不高兴的,人一不高兴就会给它些难堪,叫它别忘了,人才是它真正的“皇上”;骡子虽说也常常摆一种骄傲的架势,但也只在毛驴跟前摆摆,在马之前它总是矮着几分,如果有时和马套在一根辕下干活,它再苦再累也不敢出一声大气,而如果跟驴在一起,它就张扬多了,故意紧走几步,又慢走几步,让毛驴总跟不上它的节奏,跟骡子一块儿干活真能把驴气死;牛一直是吃苦耐劳的楷模,有几分儒雅气,也有几分大将风范,在土地上劳作,它知道守土有责的道理,虽然对它不知道变通,不抵倒南墙不回头的“牛”脾气人们略有微词,但也因为有个“老黄牛”的好名声,甚至还被文人们概括了一个“黄牛”精神,人们就一直对这个劳苦功高的功臣谦让着,牛便怀着功高盖主的心态一直很“牛”。
我在明代《便民图纂》的耕地图中看到的是一人扶犁,驾着两头牛;在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耙地图中,看到一个农民站在耙上,吆着两头牛;还有一块魏晋墓砖上是一头牛在拉着一个坐在耙上的人耙地;在酒泉石庙子滩魏晋墓砖壁画上,我看到的是一个人站着耙地,一头牛,鼓足了劲,这从它用力的尾巴上可以看出来;陕西唐代李寿墓壁画中的耧耕图,是一头牛小跑着拉着耧,人在后面扶着耧,也是压着耧,仿佛耧铃声还在急促地响着……还是在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中,我看到了耕种图,都是二牛抬杠,一人扶犁,犁是右手扶的,左手则举着鞭子,那鞭子在空中晃着,我想并不一定会落到牛身上,它只是告诉牛,该出力的时候别偷懒;而在陕西米脂汉墓画像石牛耕图中,两头牛拉着长长的四角框架长直辕,后面的人则双手扶犁,看那犁的样子和现在的铁步犁差不多;嘉峪关新城西晋屯垦画像砖牛耕图,敦煌莫高窟第6窟五代耕牛图,第61窟宋代犁耕图,第146窟五代牛耕图,第445窟的唐代牛耕图,第449窟宋代犁耕图,敦煌榆林窟第25窟中唐代犁耕图,雍正《耕织图》中的耙地图,清代顺宁府《倮黑图》中的耕作图中,全都是牛的身影,即使想打个马虎眼,把牛认成驴都不行,因为那两只角高高地翘着,仿佛你认错了它,牛就会举着犄角冲过来似的。那么,驴到哪里去了?看来驴要想在“青史”上留名是难了,不仅在这些权威的“史册”里没有驴的影子,而且在文字中也没有表扬驴的话,马替人们出了力下了苦,还有个成语叫“汗马功劳”,牛为人们流了汗就有了“老黄牛精神”,而驴呢?什么说法都没有。
那就让我给毛驴说几句好话吧。虽然毛驴没有大牲口那么高大,或者说没有骡马那么英俊好看,他个头小,形象不起眼,但它却比大牲口脾气好,不管是牲口还是人,好脾气总是招人喜欢,人们就这样喜欢上了毛驴。毛驴知道自己的“小”,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大”过,很少因为待遇不公而争过什么,它只会逆来顺受俯首帖耳,给它戴上眼罩,它就能推磨,走在磨道里,就像人们给它戴了副墨镜,阳光一下子变暗了,在暗暗的磨道里,它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走着;给它套上笼套,它就能拉犁;把它驾上车辕,它就能拉车,伸长了脖子使劲的样子,有时会让人担心它会把筋骨给挣断了;如果给它匹上鞍子,它就能驮东西,比如驮粪、驮水、驮粮食,甚至驮着人去县城赶集或着翻山越岭地走亲戚,当然,驮人一般只驮女人、小孩和老人,身强力壮的人一般是跟在驴的后面,或者牵着缰绳在驴前面走,因为他们舍不得让驴辛苦。偶有一个大男人骑在毛驴身上,人们就会骂他“懒松”,一个不知道惜疼驴的人,驴就会不惜疼他。毛驴真正是劳苦功高啊!
布封在《动物素描》一书中对毛驴有这样一段描写:
驴并不是一种退化的马,一种尾巴无毛的马。它既不是来自外邦,也不是突然闯入,更不是杂交而生;它像所有的动物一样有它的家族、它的种、它的类,它的血脉是纯的;虽然它的身份不那么显贵,它却与马一样优越、一新古老。驴幼年时是欢快的,甚至比较漂亮:它有几分轻盈和雅致;但是,它很快就丧失了这些优势,或者由于年岁,或者由于受到恶劣的对待,它变得很迟缓、难以管教、愚玩固执;尽管它通常受到粗暴的对待,它仍依恋主人:它从老远就感到这一点,将他区别于所有的别的人。它也能认出自己习惯居住的地方和经常走的路。
它眼睛尖、味觉好、耳朵灵,这一切又有助于将它置于最羞怯的动物之列。按人们的惯常说法,它们都有敏锐的听觉和长耳朵。当我们让它驮重物时,它侧过头,垂下耳朵。当我们太使它难受时,它张开嘴,以一种很厌恶的方式撅着嘴唇,一动不动。而当它侧身躺着时,假如我们摁住它的脑袋把它的一只眼睛贴在地上,用一块石头或木头遮住另一只眼睛时,它将会保持这种姿势,一动不动,也不晃动挣扎。它像马一样步行、小跑、奔走;不过所有这些动作比马要小、要慢得多。尽管它起先能够以较快的事变奔跑,但是它不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连续跑完一段路程;不管采取什么步我前进,要是我们赶它,它很快就会疲惫不堪。
当然,布封说的是他在法国见到的毛驴。法国的毛驴,我没见过,但根据他的描写,身处法国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毛驴和我老家的毛驴处境差不多,区别在于布封的毛驴听的是法语的呵斥,我的毛驴听的是汉语的吆喝,准确地说我的毛驴只听得懂土话。
毛驴有时候会吼上一两嗓子,有时高亢,有时低沉,有时悲怆,有时欢快,种过庄稼的人没有听不懂驴的话的。我曾为毛驴写过几首小诗,其中有一首叫《饮驴》:
走吧我的毛驴,咱家里没水,但不能把你渴死村外的那条小河,能苦死蛤蟆,可那毕竟是水啊趟过这厚厚的黄土,你去喝一口吧,再苦也别吐出来生在个苦字上,你就得忍着点,忍住这一个个十年九旱至于你仰天大吼,我不会怪你,我早都想这么吼一声了只是天上没水,再吼也无非是,吼出自己的眼泪好在满肚子的苦水,也长力气,喝完了我们还去种田还有一首叫《毛驴老了》:
帮父亲耕了多年地的毛驴老了,它的老是从它前腿跪地,直到父亲从后面使足了劲,才把车子拉上坡的那天开始的,那天父亲搂着毛驴的瘦腿,像搂着一个老朋友的胳膊,父亲说老了咱俩都老了,现在它或许知道自己不中用了,水不好好喝草也不好好吃,穿了一辈子的破皮袄,磨光了毛的地方露出巴掌大的伤疤,我几次让父亲把它卖掉,但几次父亲都把它牵了回来,像早年被老人逼着离婚的两个年轻人,早上出去晚上又怯怯地回来了,那天我从屋里出来,它把干枯的脑袋搭在低矮的圈墙上,声音颤抖着向我呼唤了几声,那么苍凉忧伤,父亲说他知道毛驴想说什么。
乡村的粮食
据考古发掘可知,从春秋战国时期起,粟是北方的首要粮食作物。在河南洛阳就曾出土过西汉时的粟子。粟,古代称禾,其籽实称小米。粟的种历史悠久,它是从狗尾草一类野生植物驯化而来的。考古发掘表明,新疆孔雀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炭化小麦距今已有4乡乡乡年之久。小麦起源于西北干旱地区,西周时传播到淮北平原。公元前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已有小麦的栽培。到明代,小麦的种植几乎遍及全国,在粮食作物中的地位仅次于水稻,成为我国北方的主粮之一。在甘肃大地湾发现的黍,是我国最古老的黍,距今约7乡乡乡年。黍在我国黄河流域首先被驯化,陇中黄土高原是黍的原生地之一。
这些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多数人的吃饭已不成问题,因而也就吃饱了肚子便忘了饿,正如人们习惯于好了伤疤忘了疼,不仅城里的下水道、垃圾堆上有白白的馒头扔在那里,城里的餐桌上剩下的饭菜更是被毫不心疼地倒掉。如果说有些城里人是不知道粮食的来历,不知道“粒粒皆辛苦”,只知道面是从粮店里来的,菜是菜摊上来的,那么乡下的孩子应该是见到过种田的艰辛的,甚至知道粮食成长的每一个细节,但现在乡下的孩子却也可以随手扔馒头了。
与此同时,人们对种粮的积极性越来越显出冷漠的态度,比如在农村,人们宁可去城里打工,也不愿意种地,因为种田既辛苦,且投资大,收益小,种一年田的收入不入打几个月的工,因此,在城郊的土地越来越紧张的同时,一些偏远地方的土地却开始出现撂荒的现象。在人们的观念里以为只要有了钱,就不愁买不到粮,就不会挨饿,当然天下粮食富足时可以用钱买粮,但天下无粮,你从哪里去买?守着大堆的钱还是要饿肚子的。
一旦一些地方出现旱情,赤日炎炎,禾苗干枯,好多年已不为粮食发愁的农民,似乎这才发现:原来家里的存粮其实顶不了几年,粮食的危机转眼间已逼到了门槛上。天旱了,缺粮了,有些人这才思考粮食问题,这才疾呼要节约粮食,有些老人这才开始给孩子们讲大饥荒的经历,显出一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样子。
其实,全世界一直都非常关心粮食问题。因为,受城市扩大、土地荒漠化和缺水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可耕种土地面积明显减少。过去几十年间,人类一直在同饥饿做斗争。尽管全球处于饥饿状态的总人数已经从197乡年的96亿人降到现在的8亿人,但饥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仍高达13%左右。粮食短缺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显得尤其突出。据估算,发展中国家有1,5的人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在非洲地区,有13的儿童长期营养不良。全世界每年有6乡乡万学龄前儿童因饥饿而夭折。目前全球约3乡个国家陷入粮食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乡届大会决定从1981年起,把每年的1乡月16日定为“世界粮食日”,旨在唤起公众注意长期存在的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粮食短缺问题,敦促各国政府和人民采取行动,增加粮食生产,更合理地进行粮食分配,努力发展粮食生产,与饥饿和营养不良作斗争。
不论任何时候,粮食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如果哪一天世界上没有了粮食,就像没有了水和空气一样,人类将何以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