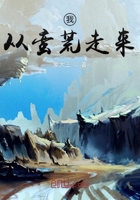说起来文静真的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尽管她比莲花村的任何一个孩子都盼望成为一个被资助儿童,尽管她比莲花村的任何一个孩子都懂得,成为被资助儿童在她的一生中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她还是耐心地等待着,耐心地帮着孩子们阅读他们的外国信,耐心地陪着孩子们欣赏他们的外国礼物。尽管她已经在心里问过自己一千遍一万遍:“为什么,为什么还没有我的外国信和外国礼物呢?”可是,她却一次也没有拿这个问题去打搅过她的父亲。
而文静爹呢,眼看着莲花村的孩子们一个又一个地收到了外国信,就只剩下了文静一个。他心里是又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国际计划的项目到底实施了,而不再是纸上谈兵。着急的是,他家的表填得只会比别人好,他家的表交得还比别人早,可他家的外国信怎么就会到得比别人家的晚呢?紧接着,文静爹又眼巴巴地看见莲花村的孩子们一个又一个地收到了外国礼物,又只甩下了文静一个。他的心里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这些外国资助者还真的是些有爱心的好人,莲花村的孩子们总算是有了新的希望。忧的是,这些爱心怎么就是迟迟不肯落到他家文静的头上呢?
但是,正像文静不愿意打搅她爹一样,文静爹也没有和文静提起这事儿,毕竟,他自己也说不清这里面的原因。毕竟,这是一件让全家都不开心的事情。
文静奶奶本来对这事儿就不赞成,虽然因为守着学校,孩子们一天到晚地吵吵着,她也听了一点半点的,但是,她却觉得没有那些外国信,没有那些外国礼物,更省心。而文静娘呢,对这事儿倒是了解得清清楚楚。可是,当初,这事儿是文静和文静爹商量着决定的,既然文静爹都没有提起,她也不好多插嘴。
所以,就一直等到春儿爹来,才打破了文静家这表面的平静。
先是文静忍不住了,说:“为啥要让我去劝甜杏呢?俺家是填了表的,她家又没填。”
接着,文静爹也沉不住气了,问:“莫非俺家文静也和甜杏一样,当不成被资助儿童了?”
来的时候,春儿爹光顾着想甜杏家的事儿,竟然忘了文静家的事儿。其实,这回为甜杏家的事儿去县上,他还真是问过周干部,为什么莲花村所有填了表照了相的孩子都收到了外国信和外国礼物,就文静一个人什么都没有收到呢?
人家周干部也回答得风趣,说:“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那外国和外国也不同,有路远的,也有路近的。那外国人和外国人也不同,有性子急的,也有性子慢的。所以呢,文静家也用不着太着急。俗话说,好戏在后头,说不定文静家等到最后,还能等来个大金娃娃呢!”
这会儿,看见文静爷儿俩着急,春儿爹就赶紧把县上周干部说的那番话一字不落地对他们说了一遍。
文静和文静爹本来就捂着个热火罐不想让它凉了,现在听春儿爹这么一说,自然觉得有道理。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也就踏踏实实地继续等着,也就商商量量地准备去给甜杏家做思想工作。
不过,还没等到文静爷儿俩商量好怎么去跟甜杏爷儿俩说,也就是春儿爹来文静家的第二天,李乡邮员就把文静家的“大金娃娃”给送来了。
当时,文静和文静爹真是喜出望外,只顾了又是沏茶又是留饭的,一直等到把李乡邮员送出了院门,这才想起来去拆那封盼星星盼月亮,差点儿盼白了头发的外国信。
拆开外面的大信封,文静家的“大金娃娃”果然和别人家的不同。里面不仅有一个写着许多外国字的小信封,还有一张写着字的纸,看署名好象是县上的周干部写给文静爹的信。
周干部在信上说,寄给文静的这封外国信是昨天刚刚收到的,收到后他和负责翻译的陈干部就立刻向县上的有关领导做了请示汇报,并且遵照领导的指示,给北京的中国交流协会和国际计划组织的中国分部通了电话。但是,在通了几次电话,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还是没有结果。为此,他并代表县上的有关领导,向文静家表示最大的遗憾和歉意。希望文静爹能够理解并做好文静的思想工作。同时,对文静爹以往帮助落实国际计划项目的行动表示感谢,希望他能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他们的工作。
文静爹把这封信看了两遍,还是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反过来却问一直守在他身边的文静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县上的周干部干嘛这么客气,又干嘛跟我道歉呢?”
因为文静爹看第二遍时,不知不觉地念了出来,而且还念得很慢。所以,信里的内容文静已经知道得差不多了。文静虽然小,却比她爹有灵性,凭直觉,她就预感到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到底怎么个不好法儿,她一下子也说不清。在这之前,她也曾有过类似的预感,那是因为自己的外国信迟迟没有到来。可是,现在,这封外国信不是已经实实在在的摆在他们的面前了吗?难道仅仅因为这封外国信来得比别的孩子晚了些,县上的周干部才会专门写了这封表示道歉的信?文静爹和县上的周干部素昧平生,甚至不认识县上的任何干部,周干部为什么会对文静家这么客气?何况,这外国信来迟了,也不是他周干部或者县上任何人的错儿呀?
难道文静家的这个“大金娃娃”真的与众不同?或者是出了什么问题?文静看见她爹还在坐着发呆,就把那个写着外国字的小信封拿起来,掏出里面的信瓤,交给她爹说:“别管周干部是什么意思了,咱先看看这外国信上都说了些啥。”
看起来,文静的这封外国信的确与众不同。莲花村其他孩子收到的外国信,都是密密麻麻的一大张,有的还写了两张。可文静的这一封,却只有简简单单的几句:
尊敬的先生:
我很高兴收到你们寄来的莲花村被资助儿童的照片和资料。但是,我很奇怪,为什么需要我资助的儿童的父亲是一位教师。在我们的国家里,教师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他们的收入也是非常丰厚的。我是一名科学工作者,我希望把我不多的收入资助给最需要帮助的穷苦农民的孩子。
和县上周干部那封十分客气却又绕来绕去的信不同,文静爹只看了一遍,文静也只听了一遍,爷儿俩就全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
文静成为被资助儿童的资格被取消了,就因为她爹是个代课老师,就因为在外国老师的收入“非常丰厚”!
文静终于哭了。多少天来,她一直憋在心里的委屈,多少天来,那一直被希望挡住的泪水,此刻,就像决了堤的洪水一般汹涌而出,滔滔不绝。
文静爹终于傻了。人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为莲花村的孩子们付出了那么多,为国际计划的项目付出了那么多,到头来,却偏偏是为了他的缘故,独独甩下了他家的文静。你叫他如何能够想得通?你又叫他如何面对自己的闺女?
要不是文静娘悄悄地去把春儿爹找了来,这爷儿俩饭也不吃水也不喝的,还不知道要伤心到啥时候呢。
可是,春儿爹来了又有什么用?他能让那个外国资助者改变主意?他能给文静恢复被资助儿童的资格?他能做到连县上的周干部也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那天晚上,春儿爹也就只能一言不发地坐在教室里,一会儿看着那封外国信发傻,一会儿又听着文静的哭声叹气。
所以,那天晚上,文静家的哭声就和甜杏家的哭声交相呼应,此起彼伏,搅得整个莲花村的大人们都跟着难过,搅得所有莲花村小学的孩子们都没了笑声。
不过,到了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文静却不哭了。她睁着肿得像桃子的眼睛对她爹说:
“爹,咱不能就这么算了,咱得找县上讨个说法儿。”
文静爹以为她是说说而已,又始终认为是自己对不起闺女。所以,就点点头顺着她说:“是啊,是得要讨个说法儿。”
接下来的一个上午,文静爹忙着给一到三年级的学生上课,文静娘体谅文静心情不好不肯叫她干活,就连文静奶奶也一边咳嗽着一边自己把文静妹妹尿湿的褥子拿到院子里去晾晒。所以,一直到吃午饭的时候,文静家才发现,文静不见了。
文静家正急得团团转时,春儿来了,交给文静爹一张小纸条,上面是文静写的字:爹、娘:我去县上找周干部。别担心,我认识路,我还带了一把砍刀。
文静爹问春儿:“文静真的去县上了?”
春儿点点头。
文静爹又问:“文静啥时走的?”
春儿说:“一大早就走了。”
文静娘埋怨说:“你咋不早说呢?”
春儿委屈地嘟哝道:“她不让我早说麽。”
文静爹不说话了,这事儿怪不着人家春儿。他只是琢磨着,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文静应该早就走到了乡里,或者已经搭上了去县上的班车。不过,文静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坐班车的可能性不大。只能是接着从公路走到县里去。尽管公路比山路好走,尽管公路没有山路偏僻,可文静毕竟还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呀。那几十里的路程她能坚持到底吗?要是走到半路走不动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办?那几十里的路程,就算是大人也要走上一天半日的。要是她走到天黑还到不了县城,要是她又困又累在公路上睡着了,冻病了,甚至被过路的汽车压着了,可怎么办?还有啊,文静就早饭吃了半个棒子面馍馍,从早上一直到深夜,甚至还要等到明天,还要走那么远的路,她不会被累坏也会被饿坏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