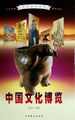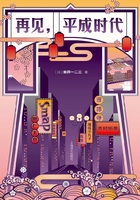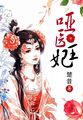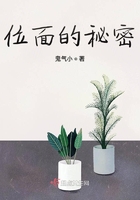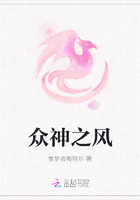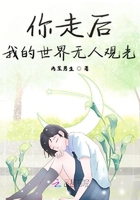拜会胡适是张爱玲文学创作上的一次寻根,是她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一次有限度的认同。在她追忆与胡适交往的散文《忆胡适之》中,鉴于友人炎权有“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一说,张爱玲针对胡适和“五四”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时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通译荣格)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与弗洛伊德齐名。不免联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倒又反过来仍旧信奉他。
在这里,张爱玲并未简单地因在国外的名声大小就下判断,而是根据在中国新文化发展建设过程中的实际贡献肯定了胡适,肯定了五四的价值和影响,批评国人不应该在成功后就无情地舍弃了曾经的领袖。须知林语堂由于用英文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小说和著作而在英美屡获好评,曾经是她少年时代仰慕的偶像和追随的榜样,但她能够跳出个人的好恶,做出较全面的评价,正反映她有一种难得的历史大眼光,也说明她是把自己放在新文学的大潮流中的。自然,这也同她本人接受的影响有关。可以说她正是五四运动某种程度上的受益者。她母亲就是深受五四精神熏陶的新派女性,否则张爱玲就不可能享受到西式教育,不可能有新旧搀半的驳杂的知识,也不可能有跳到传统生活圈子之外打量中国人的清醒和睿智。
不过,张爱玲并非对五四的一切都全盘接受,1957年间世的《五四遗事》从另一角度表明了她的态度。这是张爱玲所有作品中唯一以五四运动为背景的小说,但是她并没有像一般人写五四那样,着眼于人们如何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等,或者大唱赞歌,或者猛烈攻击旧制度旧传统。小说独辟蹊径,以戏谑的口吻娓娓叙说了一个故事,深入挖掘了这场波及全国各领域的大运动中各色弄潮儿们的性格心理,多多少少“幽了一默”。这在她其实也不是头一遭,她曾在一篇谈音乐的散文中借比喻描摹交响乐,小小地刺了一下五四运动:“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喊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以张爱玲那种清婉幽独的文人怀抱,只怕对五四运动大规模的轰轰烈烈永远不以为然。在《五四遗事》里,这种挑剔、不满的眼光是一致的。她犀利地揭示出,五四一代人当年的对抗传统,寻求现代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彻底的。许多自命为“现代”的青年往往只学到了“现代”的皮毛,甚至有的人,便如小说中的罗一样,打着“现代”的招牌,守着传统的货色,往往绕了一圈,最后依然回归到传统的生活方式中来。她并以戏谑的笔触,描绘了五四时代的风情:“称未嫁的女子为‘密斯’也是时髦”;“这是一九二四年,眼镜正人时。交际明星戴眼镜,新嫁娘戴蓝眼镜,连咸肉庄(指下等妓院)上的妓女都戴眼镜,冒充女学生”;等等,不一而足。这均昭示出张爱玲对待五四的种种腹诽。张爱玲并非不能容忍更新,但她反对只在形式上求新。如前文所论及的《更衣记》中的借题发挥:“时装的日新月异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人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只能创造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个人住在个人的衣服里。”
事实上,张爱玲能认同于五四运动的,只是其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一翼。正是基于这个契合点,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也发挥过历史作用、并仍然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潮,再度将张爱玲推上了成功的顶峰。
就像前面提到过的,由于张爱玲的种种情况,她不可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流中占有一席之地。加上1952年的出走,她在大陆文坛的影响已寿终止寝,那个时代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几乎找不到张爱玲的名字。改变这种局面,第一次给予张爱玲以高度评价的,是同样有着自由主义文化背景的夏志清兄弟。旅美华裔学者夏志清,首先在其用英文写作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专章评述了张爱玲的作品,并且给了她最多的篇幅(甚至远远超过给鲁迅的)。1957年,他的兄长、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文学杂志》的创办者夏济安把这部分翻译成中文,分别以《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为题发表在自己的刊物上。夏志清的总体评价是相当高的,他说:“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尔(Katherine Mansfield),安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o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一些具体作品也获得了上佳的评语:“《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而《金锁记》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正是在夏氏兄弟的热情推崇和大力引荐下,六七十年代以后在台湾逐渐兴起了一股“张爱玲热”,涌现出一大批“张迷”。
这一次热潮对飘零在美国的张爱玲是重新振作的大好机会。首先,她的中文作品找到了又一个发表园地,同时也大大改善了她的经济状况。因为随着她的重新走红,台港纷纷重印她早年在沦陷区时的作品,版税的收入对张爱玲拮据的生活是一个不小的帮助。人们本来期待她重出江湖,能够以更上乘的新作酬劳读者,但事实是,张爱玲几乎没有新作,有的只是对旧作的改写。1968年,台湾皇冠杂志社重印出版《张爱玲小说集》,其中《怨女》、《半生缘》两部作品,就是在原有小说的基础上经过或大或小的修改的。
《半生缘》的前身是张爱玲以梁京的笔名在《亦报》上连载的《十八春》。张爱玲对这部小说的改动主要在几个方面。一是把其中当时为迎合时势而写的一些不适宜的话统统去掉。例如在原书中有一个场景,世钧在阳台上听弄堂里一群人练习一支歌,其中有一句老也唱不对,他们便把那一句唱了又唱,连唱一二十遍。听着听着,“世钧忽然觉得很感动,他觉得有些心酸,而且自己深深地感到惭愧了。他就是这时候下了决心,一定要加紧学习,无论如何要把思想搞通它……”这样直白而没有遮拦的话简直像某个左翼作家的笔触,当然给删掉了。二是修改了各个人物的结局:叔惠不是去了解放区复又回来,而是变成了去美国留学回来;曼祯、慕瑾、世钧和翠芝也并没有齐赴东北去为国家社会做贡献……从而使整部小说的风格更加统一,也更符合张爱玲一向以来的创作观。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曾经说过:“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这个评析也同样适用于翠芝,原来写这个传统大家庭里的少奶奶,甚至都没经受过什么时代的洗礼,便也空穴来风地有了这样为国家为民族的豪情,实在有点不合情理。三是修改了小说的结尾,由“光明性的尾巴”一变而为张爱玲一贯喜欢的“情绪性的结尾”。小说在曼祯和世钧相隔14年后的邂逅中结束了。小说结尾叙完顾沈二人的邂逅后这样写道——
她一直知道的。是她说的,他们回不去了。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今天老是迷惘,他是跟时间在挣扎。从前最后一次见面,至少是突如其来的,没有诀别。今天从这里走出去,却是永别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的一样。
世钧和曼贞14年的生死恋便这样轻描淡写的一笔勾销了,还能怎么样呢?——“我们回不去了。”留给读者的是一声深长的叹息,一种不甘心,一种无以名状的哀凉。这正是张爱玲希望留下的。这种回味悠长的情绪是她始终钟爱的:“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J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所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
《怨女》严格说来并不是直接由《金锁记》改写而来,而是由它的英文本翻译过来的。英文本即前面提到过的《粉泪》(Pink Tears),未能出版。以后张爱玲又把书名改为《北地胭脂》(Rouge of the North),仍未找到出版社。一直到1967年,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这部小说才由英国的凯赛尔出版社推出,但在英国没引起批评界注意,即使有少量评论,也多是负面的,甚至有一个书评人说女主人公银娣让人“作呕”。但中文本的《怨女》在艺术上却仍然保留了张爱玲一贯的特色,不失为一部佳作。
与《金锁记》相比,《怨女》的篇幅长了很多,由一个三万多字的中篇变成了十万多字的长篇。1992年张爱玲在她的《张爱玲自选集<序>》中说:“《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被金钱的枷锁锁住一生并用这把枷锁砍杀了自己的至亲至爱。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以后我又以此为基础,重新写出了《怨女》。我就喜欢那被经济和情欲扭曲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怨女的苍凉,我觉着在那里面,我说出了我最想说的话。”可见张爱玲重写这部作品时,是有意为之的。
她的重写主要体现在对女主角银娣的重新塑造上。从七巧到银娣,最根本的变化是,如批评家指出的,“女主人公已经由一个心理变态的疯子——一个悲剧英雄——变成了一个人情之常可以解释的小奸小坏的庸常之辈。”《金锁记》中曹七巧的许多举动都是常理不能容的,只能用疯狂来解释。《怨女》在这方面明显弱化了。首先,小说一开始用了三章的篇幅介绍了在《金锁记》中只作为背景来写的女主人公出阁前的生活和订亲的经过,更清楚地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更多地写了银娣天性中良善和温情的一面,如对自己的外公外婆的亲情,以及与药店伙计小刘的感情。其次,原来后半部里主要写的关于长安的故事,在这里完全删除——因为在《金锁记》里,七巧出于变态的情欲和嫉妒破坏女儿的婚姻,正是疯狂的典型表现。而为了写银娣的“凡人性”,张爱玲在《怨女》里增加或详写了她与三爷四次调情的经过。尤其在第二次调情后,银娣怕事情败露而上吊自杀的情节,更是活脱脱写出了一个旧式家庭出轨的少奶奶又羞又怕的寻常心理。
所有的这些改动其实与张爱玲的创作思想是一致的。她在当年回答傅雷批评的《自己的文章》里曾经说过:“极端病态和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是一种启示。”《金锁记》中的曹七巧“30年来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怨女》中的银娣却不过是一个为旧式婚姻埋葬的普通女子。“怨”是她的主要特征,而这个“怨”正是对传统婚姻的“怨”,对一个不能得到的男人的“怨”。
小说另一个重要的修改是增加了许多关于传统大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比如做寿的堂会、娶亲、分家等。其中也涉及到更多的人物,尤其通过银娣和三爷及自己儿子的两次谈话,把一个大家族内的形形色色人物的形形色色的生活细细地写了一遍。几个在《金锁记》中仅有名字的人在《怨女》中变得更加清晰有面目。像九老太爷,在《金锁记》中只有主持分家的一个场景描写,在《怨女》中则写了他更多的荒唐事,如喜欢捧女戏子、借用人生儿子。而对三爷的描写也大大增加了笔墨,不仅有直接写他的“圆光”一场,而且还通过亲戚间的评论,写了他年老后靠两个妓女养活的穷愁潦倒的局面及他最后的死在银娣心中所引起的感慨。
这所有的种种,都让我们觉得,张爱玲是在笔墨中温习已远隔江山万里的往昔。那氮氯的鸦片的气味,那由名角捧场的堂会……一切都是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仿佛在借这种细细的描摹重新到她感觉亲切的生活里去神游了一遭。她说过:“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如今这一切是完全失去了,不仅隔了几十年的光阴,而且还隔着山长水阔。在异域的迢远的梦中,她该是常常回到那种气氛以求得一点排解孤寂的温馨吧?就像《对照记》中她花了不合比例的篇幅大谈祖父母的婚姻和相关亲戚的生活一样。
《怨女》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与《金锁记》相比,它明显写得淡。张爱玲自己比较《醒世姻缘》和《海上花列传》的话,正好来评论她的这两部题材一样的小说,“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怨女》显然没有《金锁记》那样的戏剧冲突和紧张的气氛,也少了大量独具匠心的意象和比喻,更少了《金锁记》中类似电影蒙太奇手法的运用等。其实,不仅仅是《怨女》,张爱玲到美国后的后期创作,除前已提到的《半生缘》、《五四遗事》、《浮花浪蕊》,还有《相见欢》、《色·戒》,总的趋向都是越来越平淡,再见不到《传奇》中的小说那样瑰丽的色彩、奇幻的意象、精致的比喻。这当然和作家在异国居住时间日渐深长也有关,因为无论时空都离她描写的生活越来越远,只剩下越来越模糊的回忆,连当初的激情也都褪了色,洗尽铅华,归于平淡,归于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