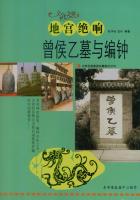例如,周作人此时便意识到:“保存国粹正可不必,反正国民性不会消灭,提倡欧化也是虚空,因为天下不会有像两粒豆那样相似的民族,叫他怎么化得过来。”周作人:《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雨天的书》,第112页。因此,“国粹欧化之争是无用的;人不能改变本性,也不能拒绝外缘,到底非大胆地是认两面不可。倘若偏执一面,以为彻底,……大家高论一番,聊以快意,其实有什么用呢?”他并且还表明:“要打破这个浑沌情形,靠外来思想的新势力是不行的,一则传统与现状各异,不能适合,二则喧宾夺主,反动必多,所以可能的方法还是自发的修正与整理”,周作人:《论小说教育》,《苦口甘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我们反对模仿古人,同时也就反对模仿西人,所反对的是一切的模仿,并不是有中外古今的区别与成见。……这便是我对于欧化问题的态度”。周作人:《国粹与欧化》,《自己的园地》,第13、12页。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周作人也逐渐认识到“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坏的传统思想,自然很多。我们应当想法除去他,超越善恶而又无可排除的传统,却也未必少”,周作人:《〈扬鞭集〉序》,《谈龙集》,第40页。这种观点明显较此前更为平和。1922年,当沈尹默在致其信中说:“前人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绫罗绸缎,只没有剪制成衣,此时正应该利用他,下一番裁缝工夫,莫只作那裂帛撕扇的快意事。蔑视经验,是我们的愚陋;抹杀前人,是我们的罪过。”周作人也认为这一见解“实在很是确当”。周作人:《古文学》,《自己的园地》,第21页。他还澄清说:“说到古文,这本来并不是全要不得的东西,正如前清的一套衣冠,自小衫裤以至袍褂大帽,有许多原是可用的材料,只是不能再那样的穿戴,而且还穿到汗污油腻。新文学运动的时候,虽然有人嚷嚷,把这衣冠撕碎了扔到茅厕里完事,可是大家也不曾这么做,只是脱光了衣服,像我也是其一”。周作人:《序》,《药堂杂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这一方面既以亲身经历说明新文化派并非所谓“全盘反传统”,另一方面又明确提出了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主张。
又如,鲁迅后来也深刻意识到:“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鲁迅:《〈浮士德与城〉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355页。他还说:“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鲁迅:《“感旧”以后(上)》,《鲁迅全集》第5卷,第329页。“我已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鲁迅:《〈引玉集〉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419页。在总结艺术创作经验的过程中,鲁迅更指出:“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柢,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鲁迅:《致魏猛克》,《鲁迅全集》第12卷,第381页。“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鲁迅:《〈木刻纪程〉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第48页。譬如木刻,他便明确提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鲁迅:《致李桦第三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45页。他还曾称赞陶元庆的绘画“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鲁迅:《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鲁迅全集》第3卷,第550页。同时,鲁迅还针对有些青年对继承传统的顾虑精辟地分析说:“‘旧形式的采用’的问题,如果平心静气的讨论起来,在现在,我想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熔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机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鲁迅:《“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全集》第6卷,第22—23页。这种充满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无疑代表了当时人们探索中西文化问题的最高认识。
这一时期,前期十分激进的钱玄同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也不断深化。这里首先必须澄清的是,即使在他竭力主张“反孔”之时,他也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他曾经公开宣称“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钱玄同:《论世界语与文学》,《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3页。并在日记中赞成同门朱蓬仙的看法,认为“孔子以前,榛榛狉狉,极为野蛮。孔子修明礼教,拨乱反正”,有文明开化的功劳。《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3月26日条,第1563页。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孔丘确是圣人,因为他是创新的,不是传统的”,《钱玄同日记》第5册,1922年10月1日条,第2292页。“今日《甲寅》日刊有李守常《论真理》,其言曰‘孔、佛、耶学说,有几分合于真理者,我则取之,否则斥之’,其说甚正”。《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2月2日条,第1541页。他甚至还认为“陈独秀、胡适之诸人抵斥孔氏太过”。《钱玄同日记》第5册,1923年4月1日条,第2617页。很明显,钱玄同并未完全否定孔子的历史价值,他只是反对在现实生活中不加择取地任意套用孔子学说。
除此之外,钱玄同还十分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部分。他对于先秦诸子百家,司马迁、刘知几的史学,王充、李贽的异端思想,永嘉学派与颜李学派,以及《水浒》、《三国》、《红楼》、《儒林外史》等小说,都曾予以积极肯定。有些评价还很高,如他赞美《国风》“很真很美,……应该大大地表彰它”;钱玄同:《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03页。他还认为司马迁《史记》“深明历史为记载人群遥代之迹,使人得鉴既往,以明现在,以测将来,绝非帝王家谱相斫书”。《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4月14日条,第1575页。尤其是对墨子学说,钱玄同最为推崇,甚至他由钱夏改名为钱玄同,也是“因厌恶阶级社会之故,无一日不受刺激,因之献身社会之心日盛一日,改名玄同,即因妄希墨子之故”。《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4月14日条,第1575页。其挚友黎锦熙后来也评价他:“钱先生的思想人格,若照先秦诸子的旧说法,是‘逃杨而归儒,逃儒而归墨’的”,“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处,还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功利主义’,墨家的人生观”。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89、92页。
由此可见,钱玄同始终都没有“全盘反传统”。至于他曾提出将古书“束之高阁”的主张,他也一再解释说:“从事实上观察,要叫大家都将国故‘束之高阁’,究竟是不可能的事”,钱玄同:《汉字革命与国故》,《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139页。“这自然都是指应该有这样的精神而言,自然不是真把一部一部的古书扔下毛厕或束之高阁。……据我看来,青年非不可读古书,而且为了解过去文化计,古书还是应该读它的”。钱玄同:《青年与古书》,《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43—144页。
在此期间,钱玄同还对自己发表过的偏激言论加以了深刻的反思。1920年9月25日,他即曾致信周作人表示:“我近来很觉得两年前在Sincinnieno(《新青年》罗马字母拼法——引者按)杂志上作的那些文章,太没有意思。……其实我们对于主张不同之论调,如其对方面所主张,也是二十世纪所可有,我们总该平心静气和他辩论。我近来很觉得要是拿骂王敬轩的态度来骂人,纵使所主张新到极点,终之不脱‘圣人之徒’的恶习”。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32—33页。数日后,他在致胡适信中同样也说:“我年来颇懊悔两年前的胡乱动笔,至一偶翻以前之《新青年》,自己看见旧作,辄觉惭汗无地。”钱玄同:《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95页。1921年1月1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我在两三年前专发破坏之论,近来觉得不对,杀机一起,绝无好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处而不相悖,方是正理。”《钱玄同日记》第4册,1921年1月1日条,第1916页。此后,他虽然一度愤慨于顽固守旧势力的回潮,“偏谬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但事过境迁之后,他则再次冷静下来说:“我近来思想稍有变动,回想数年前所发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今后大有‘金人三缄其口’之趋势了。”钱玄同:《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18页。黎锦熙也曾回顾钱玄同对早年作品“表示不甚满意”,“简直完全要不得”。(《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68、66页)另据王森然记,钱玄同还曾告诉他:“当时马、沈、陈、刘与自己均犯过刻薄幼稚病。”并反思说:“余之思想,颇类梁任公,常变更主张,如飘蓬之无定向也”。见《钱玄同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第344—345页。
正是在这种不断反思的基础上,钱玄同的中西文化观逐渐趋于成熟。他不仅曾经呼吁:“我们对于一切学问事业,固然不‘保存国粹’,也无所谓‘输入欧化’。总之趋向较合真理的去学去做,那就不错。”钱玄同:《论中国旧戏之应废》,《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51页。而且还进一步阐释:“我常说‘欧化’,似乎颇有‘媚外’之嫌,其实我但指‘少数合理之欧’而言之耳。‘多数之欧’,不合理者甚多,此实无‘化’之必要”。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68页。例如,“我以为纵然发现了外国人的铁床上有了臭虫而不扑灭,但我们绝不应该效尤,说我们木床上发见的臭虫也应该培养,甚至说应将铁床上的臭虫捉来放在木床上也。所以外国女人虽然有头发,但中国女人并非不可剪发;……外国女人虽穿锐头高跟的鞋子,但中国女人并非不可穿宽头平底的鞋子;……诸如此类,我的见解都是如此”。钱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7月17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62页。该函原系于1923年,有误,详参拙文《关于钱玄同几封往来书信的系年考辨》,《东方论坛》2006年第2期。很显然,钱玄同经过反思,对“欧化”的态度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与此同时,钱玄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也渐趋平实。他明确提出:“我们还应该查考明白,祖先究竟种了多少恶因;还有,祖先于恶因之外,是否也曾略种了些善因。查考明白了,对于甚多的恶因,应该尽力芟夷;对于仅有的善因,更应该竭诚向邻家去借清水和肥料来尽力浇灌,竭力培植。凡此恶因或善因的账,记在古书上的很不少(自然不能说大全),要做查账委员大人,便有读古书之必要了。……只要是用研究历史的态度来读古书,都是很正常的。”钱玄同:《青年与古书》,《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45页。由此出发,他积极支持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他说:“我以为‘国故’这样东西,当他人类学地质学之类研究研究,也是好的,而且亦是应该研究的。”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8页。并且还明确表示:“我是喜欢研究‘国故整理问题’的”,钱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4月8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76页。该函原系于1926年,有误,详参拙文《关于钱玄同几封往来书信的系年考辨》,《东方论坛》2006年第2期。“整理国故一部分的事,我也还想做做”。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9页。至于沈尹默所提倡的继承前人遗产,他也予以了十分宽容的理解:
尹默回国了。他近来的议论,我颇嫌他过于“笃旧”,不甚赞成。但我以为这完全是他的自由,应该让他发展。况且他对于“旧”是确有心得的,虽他自己的主张似乎太单调了,但我还觉得他今后的“旧成绩”总有一部分可以供给“新的”,为材料之补充。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很正当,很应该的。但即使盲目地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此意你以为然否?但我——钱玄同——个人的态度,则两年来早已变成“古今中外派”了。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75页。
20年代后期苦雨斋聚会,前排左起:沈士远、刘半农、马裕藻、徐祖正、钱玄同。后排左起: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苏民生。当时章门弟子经常在此聚谈。
由是观之,钱玄同虽然在公开场合屡屡以一个激进者的形象出现,且曾发表过不少偏激言论,但在其日记或致友人私函中,他则显得较为客观平和。这显然意味着他的那些偏激言论,主要是作为一种思想斗争的口号而提出,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他的学术观点。就中西文化观而言,尽管由于个人性情以及时局变化的影响,他这一时期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往往大起大落、几经反复,关于钱玄同这一时期文化思想的变化,可详参刘贵福:《钱玄同文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2000年博士论文)、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01年博士论文)。但从总体趋势来看,无疑是不断趋向成熟。
综上所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章门弟子的思想倾向尽管有激进、保守、温和之别,甚至因此最终导致了同门的分化,但是他们的思想主张无一不是基于自己的深刻思考,都堪称近代文化探索历程中的可贵思想。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正是他们的这种相互激荡与自我反思,不断丰富和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