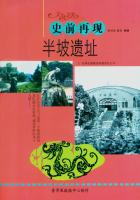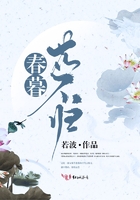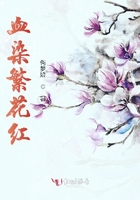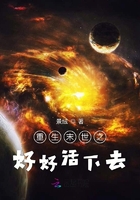王徽之是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也是东晋一位名士,为人清雅放旷。《世说新语》中记载,他曾借别人的空宅居住,住下后便令人种竹,有人问他不嫌麻烦吗?他指着竹说:“何可一日无此君?”另有一次,王徽之在山阴时,夜里下起了大雪,他忽然想见朋友戴逵,当时戴居地很远,但他依然连夜乘小船前往,长途跋涉后到达朋友住处,却连门也没有进又直接返回,人问其故。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其放诞疏狂可见一斑。但魏晋士人能放诞如斯,大多也能深情至极。王徽之与弟弟王献之感情很好,献之去世后,他坐在弟弟的灵床上,取过献之最爱的琴调弦欲弹,几不成调,遂把琴掷于地上,说:“子敬!子敬!人琴俱亡矣。”恸绝良久,不到一个多月也去世了。
而桓伊同样是一位性情中人,他是东晋的一位高官,身为武将,曾参与著名的“淝水之战”,在谢安领导下,与谢玄、谢石共同率领晋军打败了强大的前秦军队。桓伊在音乐方面有突出的才能,当时人称他为“江左第一”。他是一流的笛子演奏家,杜牧《润州》诗中有“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之句。桓伊为人谦虚朴素,个性不事张扬,因而立有大功却从未招人忌恨。
正是晋人旷达不拘礼俗、磊落不着形迹的名士风度,才成就了这一千古琴曲。如今遥想悠悠千载的那幕场景,让我们仍心存温暖和感动。
桓伊的《梅花三弄》原谱为琴箫合奏,它十段各有小标题,其节奏较为规整,宜于合奏。全曲整段三次奏响主题,都是用手指轻点琴弦奏响“泛音”,因为清脆空灵的泛音正衬托出梅花的清雅的品质。而主题三次变奏这样的结构,也就是“三弄”之义,“为梅花三弄之调,后人以琴为三弄焉”,所谓一弄叫日、二弄穿月、三弄横江。以此来描绘梅花不惧严寒、迎风怒放、幽香溢远的气质。乐曲的引子部分亲切优美,节奏则平稳舒缓、跌宕起伏,精练地概括了全曲的基本特征。第一段是古琴在低音区出现的曲调,冷峻肃穆,勾画出一幅霜晨雪夜、草木凋零、梅花傲放的画面。前12小节以五度、六度的上下行跳进音程为特征的旋律,结合稳健有力的节奏,富有庄重的色彩,仿佛是对梅花的赞颂。后14小节多用同音重复,附点节奏的运用使旋律富于推动力,似乎梅花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晃动起来。接着便是乐曲音乐主题的第一次重现,这段优美流畅的曲调轻巧、跳荡地在这部分音乐中三次循环出现,表现出一种“风荡梅花、舞玉翻银”的意境。
《梅花三弄》在南朝至唐流传时表现的离愁别绪和怨感哀伤的情感,而在后世逐渐改变为赞美梅花凌霜傲寒、高洁不屈的节操与气质。梅花形简而格高,瓣薄并不繁复,却耐得住清寒和孤寂。山坡,高岗,墙角,梅花凝于虬干劲枝,庄重而内敛地开着,经霜愈艳、遇雪愈香,没有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在苦难中脱颖而出,缘自清高的品性、不屈的信念、执著的追求。所以,文人诗客把梅花的气质移入人的精神中,如南宋诗人卢梅坡有“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北宋诗人林逋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明朝文人钱谦益有“今夕梅魂共谁语?任他疏影蘸寒流”。花有格,人有品,以梅花借代人格,用琴音倾诉心音。而“梅为花之最清,琴为声之最清,以最清之声写最清之物,宜其有凌霜音韵也。”《梅花三弄》曲调悠扬,轻快透澈,以古琴旷古超然的声音来演绎梅花的脱俗气质,实为绝配。
现今影响最大的曲谱是虞山派《琴谱谐声》(清周显祖编,1820年刻本)中所载的琴箫合谱,以及广陵派晚期的《蕉庵琴谱》(清秦淮瀚编,1868年刊本)。前者以节奏规整见长,后者则较自由,特别是曲终前的转调令人耳目一新。1972年,此曲再经改革,保留原作音调,由王建中改编成钢琴曲,表现毛泽东诗词《咏梅》的主题。全曲将梅花之美、梅花之傲描摹得淋漓尽致,而曲后的志趣更显豁达明亮。
要弹好这首曲子,涉及到的古琴技法相当多,而且节奏疾徐及细部的处理都十分关键。最重要的还在于演奏者的文化内涵和人格修养也会影响其演奏的音乐意境,高尚者所奏之音必是清雅脱俗的,而卑劣者所奏之音一定是喑哑恶浊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梅花三弄》正是中国士人清雅气质的典型表现。
燕乐大曲《破阵乐》
音乐舞蹈的活跃与发展往往与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家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氛围浓厚,最能催生出艺术的繁花,中国历史上的大唐帝国正是这样一个花开似锦的年代。
魏晋以来,大约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南北文化、各民族文化甚至不同国度的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这一时期,东方的高丽,西方的龟兹、疏勒,南方的印度音乐等异域外族音乐纷纷涌入中土。汉代以后,宫廷或贵族们举行盛大宴会时,大都会采用大型歌舞来助兴。这类宴会音乐多称为“燕乐”或“宴乐”。自汉乐府开始,宴会音乐更多地吸收民间俗乐俗舞的营养,集中了当时最主要的音乐元素,从而成为最丰富也最能体现时代特点的音乐形式。隋、唐政治上的统一,遂使这种音乐文化上的交流融合为一体。唐代兼容并包的文化气氛使得它更容易吸收和借鉴外来音乐,更为重要的是,唐代帝王十分重视与爱好乐舞,唐代的宫廷乐舞机构十分庞大。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集中了大量技艺高超的乐舞伎人。歌舞宴乐无疑是唐代宫廷的流行风尚,而这种风尚在民间同样盛行。大量的民间艺人在街头、酒肆中献演谋生,官员、贵族的家中也蓄养歌伎舞女,寺院中还会上演有一定故事情节的歌舞戏,唐代的王公贵族、文臣武将、文人学士都以表演舞蹈为乐趣。在这种弥漫于全社会的音乐热潮中,燕乐繁盛,无论在表演形式还是艺术水平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隋唐燕乐是在宴会上表演供人欣赏和娱乐的,其最大特点是民间特色、民族融合和中外融合。
燕乐形式多样,包括声乐、器乐、舞蹈、百戏等,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多段大型歌舞,隋代称《七部乐》、《九部乐》,到唐代发展为《九部乐》、《十部乐》。“部”是表演单位,相当于“队”。唐玄宗时,又根据表演形式把燕乐分为《立部伎》和《坐部伎》两种:《立部伎》共8部,用于室外表演,《坐部伎》共6部,用于室内演出;室外表演的人数最多能到180人,最少也要60人;室内表演的人数较少,多的时候12人,最少3人。从表演顺序上看,宴会开始往往先奏《立部伎》和《坐部伎》的音乐,然后再进行其他节目的表演。
从音乐种类看,隋唐燕乐中最主要部分是来自少数民族和外国的音乐,这从《七部乐》或《十部乐》的名称上就能看出来,如《西凉乐》、《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天竺乐》、《扶南乐》、《高丽乐》等。这些外来音乐。晋代以来就流行于中原地区了,而把它们整合并统一到燕乐的表演形式之下是在隋唐。在这样的融合中。汉族传统乐器与少数民族乐器相互配合,少数民族的曲调配上了中原地区的歌词,不同的乐种相互交流,既带来了音乐总体上的繁荣,又充分保留了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精华。
弄胡琴图在隋唐燕乐中,应用最为普遍的是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如龟兹乐和西凉乐,其中又以龟兹乐最为突出。龟兹位于丝绸之路上(今新疆一带),这里因为地处东西方文化交会之地,吸收了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的音乐元素,遂形成了独具风格的龟兹乐。在唐十部乐中,龟兹乐的乐器最为丰富,既有龟兹人独有的五弦琵琶和筚篥,也有汉民族的筝和箫,还有来自羌族以及印度和波斯等民族的乐器,约有十几种之多。龟兹乐的传入,促进了中原乐器的改革。今天民间使用的许多乐器,如琵琶、腰鼓、横笛等都和龟兹乐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龟兹乐以热烈激昂著称,打击乐器占主要地位。龟兹乐舞也极具特点,注重跳跃、击掌、旋转等重节奏重速度的舞蹈动作,著名的“胡旋舞”、“胡腾舞”都是其代表。
“胡旋舞”、“胡腾舞”属于“健舞”,它们由西域传入中原,前者以“旋”为主,在舞蹈中以轻盈、快速地连续旋转取胜;后者以“腾”为主,在舞蹈中以矫健、活泼的不断腾跃动作见长。胡旋舞主要来自西域的康国、史国和米国等,隋唐燕乐《九部乐》、《十部乐》中就有“康国乐”,其舞蹈“急转如风”,就是“胡旋舞”。从相关记载来看,胡旋舞的节拍十分鲜明,奔腾欢快,多用旋转蹬踏等动作,急骤处如迅风旋过,故名“胡旋”。舞蹈者多数是在地面上表演,也有的记载是在一块毯子上,更有精妙者是在一个球上舞蹈。纵横腾跃的时候,两脚始终不离圆球,舞技十分高超,且带有一定的杂技色彩。胡旋舞有女舞也有男舞,有独舞,也有三四人共舞。此舞约在唐开元天宝年间流行宫廷、风靡中原,50年盛行不衰。胡旋舞的伴奏音乐以打击乐为主,伴奏乐器主要有鼓、笛和钹等。据说杨贵妃跳起胡旋舞时,气氛热烈,十分具有感染力,唐玄宗看到兴奋时,还亲自为她击鼓,竟至把羯鼓击破。安禄山本为胡人,身形十分肥壮,腹垂过膝,跳起胡旋舞来居然迅疾如风。也许正因为杨贵妃和安禄山擅长胡旋,而这两人又是大唐由盛及衰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于是,在后世人眼中,胡旋舞似乎成了迷惑君王的一种工具。白居易、元稹在《胡旋女》诗中都曾直指胡旋误国。这种看法自是偏激之论,一种舞蹈当然不可能颠覆一个国家,但它在盛唐时期的盛行,却直接反映出一种自由奔放的时代精神。
燕乐大曲中的《破阵乐》即为龟兹风格的作品。《破阵乐》本是隋末唐初的一种军歌,秦王李世民在大唐开国之初平定叛乱,有人就用《破阵乐》的曲调填上新词,来歌颂李世民的神勇功德,于是也称《秦王破阵乐》。李世民十分喜欢这首曲子,贞观年间,他登基后不久,在春节宴请群臣的宴会上即高奏《秦王破阵乐》,他还为这一乐舞绘制了《破阵乐舞图》,同时命魏征等人修改歌词,对原有曲调也做了进一步的改编。
唐太宗时的《秦王破阵乐》,表演者有120人,身穿铠甲,手持剑戟;舞队的队形,左面为圆,右面为方;前面为战车之阵,后面则摆开队伍,队形展开时,模拟作战的阵势。此曲的表演可谓气势如虹,据记载,“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唐太宗之后,《秦王破阵乐》的演出人数曾逐渐减少,到唐玄宗时又将它改编为更为庞大的乐舞,人数远远超过了120人,达到了数百人,但演出者已经全部是宫女了。
如果说唐太宗时的《破阵乐》还充满着征战天下、一统江山的满腔豪情,那么,唐玄宗时的《破阵乐》已经完全烘托出歌舞升平的盛世雍容气度了。
《秦王破阵乐》在当时即已名扬天下,唐玄奘取经到达印度时,印度国王就曾当面向他咨询这首乐曲的情况,言谈之间十分神往。唐穆宗与吐蕃结盟,唐使者到达吐蕃参加结盟仪式,吐蕃即奏《秦王破阵乐》来欢迎唐使者。武则天时,日本的遣唐使又将它带到了日本,至今日本还保存有《秦王破阵乐》的五弦琵琶谱、琵琶谱、筝谱、筚篥谱、笛谱等数种曲谱。
《霓裳羽衣曲》
隋唐燕乐中的大型歌舞也统称为大曲,大曲集器乐、歌舞为一身,是唐代音乐的巅峰之作。这种大型歌舞形式产生于周代的宫廷雅乐中,到汉代乐府时得到进一步完善。汉代歌舞大曲结构上分为引子(艳)、乐段(解)、结束(乱)三大部分。而唐代大曲因为融合了不同风格不同地域特色的音乐,其结构已远比汉代大曲庞大和复杂,典型的唐代大曲一般分为三大部分,每部分又包括若干段:“散序”是第一部分,节奏比较自由,纯器乐表演,有独奏、轮奏或合奏:第二部分叫“中序”,一般为慢板,以歌唱为主,器乐伴奏,有时会加入舞蹈;第三部分称“破”,以舞蹈为主,器乐伴奏,有时也加入歌唱,节奏逐渐加快,最后到极快。大曲演出一遍所费时间相当长。
据记载,唐代有46种大曲,节奏复杂,曲调丰富。大曲中有一部分叫做“法曲”。“法曲”的出现最初与佛教音乐有关,是佛门弟子所创作的世俗大曲,后又掺杂了一些道教音乐的成分,并形成清幽悠远、别具一格的艺术风味。《霓裳羽衣曲》就是最有名的法曲,也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宫廷乐舞。
传说天宝初年的中秋夜晚。圆月高悬。桂花飘香,唐玄宗正和妃嫔们在宫中赏月。方士罗公远对玄宗说:“皇上想不想到月宫里去玩?”唐玄宗说:“如何去得?”只见罗公远取一枝桂花向空中一扔,桂花立刻变成一座银桥。罗公远和唐玄宗上桥走了不远,就到了月宫。月宫里面有数百个仙女穿着白色的衣服在庭院里跳舞。优美的舞姿,悦耳的音乐,看得唐玄宗如醉如痴。唐玄宗问舞曲名字,仙女们告诉他是《霓裳羽衣曲》。于是,唐玄宗默默地记下一半乐谱。回宫后不久,恰逢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派人送来一部由西域传入的《婆罗门曲》,其中有些旋律竟与唐玄宗在月宫中听到的《霓裳羽衣曲》相似。唐玄宗大喜,便亲自加工整理,把杨敬述所献的曲子改名为《霓裳羽衣曲》。据记载,印度佛曲《婆罗门曲》从西域传入中国,确实经唐玄宗整理润色变成了《霓裳羽衣曲》,但乐谱早已失传。据史料考证。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用绸子代替羽翼起舞,就是《霓裳羽衣舞》被神化了的一种艺术形式。
《霓裳羽衣曲》是歌乐舞三者合一,结构比较庞大复杂。白居易有《霓裳羽衣歌》一诗,他在自己所做的注释中,介绍了此曲的结构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共36段。其中散序6段,器乐独奏,节奏比较舒缓,舞者处在蓄势待发的状态中;中序18段,节奏起,舞者翩然起舞,可能会伴有歌唱;曲破12段。以节奏急促的舞蹈开始,越来越快,到结尾处,节奏放慢,最后结束在一个长音上。据白居易注释,此曲的结尾颇具特色,其他乐曲结尾大都急促到戛然而止,唯有《霓裳羽衣曲》是将尾音拖长后,慢慢消失。这样的音乐处理方法却使得此曲呈现出清雅宜人、回味悠长的审美韵味。关于这首曲子的长度,白居易说是“出郭已行十五里,唯消一曲慢霓裳”,放慢节奏的霓裂曲,长度大约相当于木船开出15里,算来大约需要半个多小时,因此,正常的霓裳曲应该在20分钟至30分钟左右。
《霓裳羽衣舞》的表演服饰十分华美。曲名“霓裳羽衣”实际已经指明这一特点。舞蹈者梳着仙女式样的高高发髻,身穿孔雀羽毛织就的翠绿舞衣和彩虹色舞裙,佩戴光彩夺目的七宝首饰,恍如天宫仙子曼妙起舞。据说,由于舞者人数众多,舞蹈动作繁复激烈,在舞蹈结束后,常常会在舞池中捡拾到掉落下来的珠翠配饰。此曲的演奏乐器大都是汉民族传统的“丝竹”乐器,包括磐、箫、筝、笛、箜篌、甯粟、笙、琵琶、琴等。与隋唐燕乐中大量带有异域异族色彩的乐曲相比。《霓裳羽衣曲》可谓是一首真正具有汉地韵味的“丝竹之乐”。而在传说中,唐玄宗最初是用笛子吹奏出这首曲子的,白居易《琵琶行》中的琵琶女也曾用琵琶演奏过此曲,还有人用琴弹过它。世人评论该曲“清而近雅”,看来与这些丝竹类乐器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