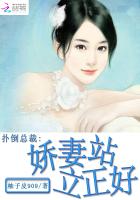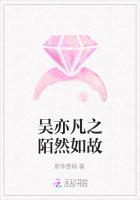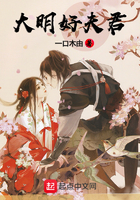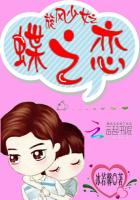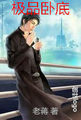今年7月7日,是我的文学恩师魏巴特尔先生去世一周年的祭日。时间过得真快,不觉已是一年。越往这个日子挨近,先生的音容笑貌愈加清晰,犹在昨天。而我作为他的学生,心绪久久地难以平静,尤其对先生的离去,每每想起便止不住地泪水潸然,进而向我心中的一座人生的高山仰望、仰望……
缘 起
我深信,人之交往于冥冥中生而有缘。既然有缘,便会在时间的长河里相遇,只是迟早的事情。
我和魏巴特尔先生的交往,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时,我在阿左旗党委工作,秘书之余,开始业余文学创作,涂鸦之类的东西,羞于示人。一次,意外地得到一册内部发行的《阿拉善民歌集》,大字排版铅印,编译者即魏巴特尔先生。虽然当时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但从书中的字里行间不难读出作为翻译者的博识与才情,以及深厚的汉语言功底和文学水平。掩卷思之,令我这个大学文科毕业生汗颜。不过,正是这一册印刷粗糙的民歌选本,让我爱不释手,渐渐读出了其中的大滋大味,所谓“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感觉对自己的创作大有裨益和启发,不妨借此而循之蹈之,写自己熟悉的牧区生活。后来,正值《戈壁》创刊,时任编辑的赵敬超组稿,我便斗胆递上一个短篇小说《暴雨》,内容大意是一对年轻的蒙古族牧民夫妻的感情纠葛,在一场突降的暴雨中得到洗礼和升华。我知道作品的稚嫩是显而易见的,投石问路而已,并不抱什么希望。没成想作品最后到了魏巴特尔先生那里,却给予肯定并且亲手进行了修改,包括主人公的名字都进行了订正。后来,就听赵敬超谈起这件事,说魏老师看好我的作品,认为潜力不错,还打听了我的一些情况。作为初涉文学创作的我,能够得到先生这样的评价,难免心潮澎湃、情绪激动,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慨。
于是,就相见了,我也从此开始尊敬地称呼先生为魏老师。至于当时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见的面,时隔多年已经记不得了,但魏老师留给我的第一印象至今未有任何改变,而且永远地固定在我的脑海里了。高大的个头,胖瘦适中,肤色略显粗黑,总是面带微笑。那么朴实,那么和蔼,那么慈祥,那么平易近人,那么善解人意,没有一丝一毫的故作姿态。要知道,那时的魏老师已经是卓有成就的作家和翻译家,尤其是在蒙汉文互译方面,在国内颇具影响,有很高的知名度。我是一个内向口拙的人,近乎于木讷,却往往留给他人一种傲慢的错觉,也因此吃了不少哑巴亏。老实说,我恰恰是自卑大于自信,见了那些所谓的显贵和名人,就头皮发紧,唯恐躲之不及,语言自然比舌头还要短半截。可是,在魏老师那里,完全没有这种心理障碍,一点都不觉得紧张,几次交往下来,已经是无话不说的老朋友了。我们谈文学、忆往事、说世态、评时事,有时候观点有异,各执其词,会毫不设防地争论一番,结果往往是“不欢而聚”,兴之所至,约几个朋友喝酒去,自然是魏老师自己掏腰包的时候多。
什么是一见如故?我想这就是了。试问天下人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永相许。现在回过头追忆,魏老师和我当属两代人,以年龄而论,魏老师大我将近二十岁,堪称尊长;以影响而论,魏老师名满国内,及至海外,而我只是走入社会没多长时间的一介书生;以学识而论,魏老师博古通今,著述甚丰,而我只是浅尝辄止,学问更是谈不上。不过,我们对文学的爱好与追求,却是一致的。那时国人尚不知手机和电脑为何物,文学也没有被边缘化,甚至还很神圣,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尤其是各种流派和主义此消彼长,你方唱罢我登场,新写实、先锋派、口语化写作等等不一而足,热闹非凡。魏老师对此却是淡定的,有他自己的独到的关于文学的主张和见解,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其实,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类似于一棵树牢牢地扎实了自己的根,“风雨不动安如山”。魏老师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始终保持着浓厚的阅读和研究的兴趣。我想,这和他最初接触文学的时代和环境密切相关。每逢谈及文学,魏老师言必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言必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等等。在他的作品中,同样也不难看出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如短篇小说《神枪手》《他在门前拴了一条狼》,长篇章回体小说《阿拉善传说》等。每逢这种时候,一向谦和、优雅的魏老师,似乎变得不那么谦和了,很快焕发出另一种神采,或侃侃而谈,或娓娓道来,人一下子变得激情飞扬了。我倒是真正地虚心了下来,也真正地成了小学生,那是真正的洗耳恭听,同时暗自叹服魏老师那超拔的记忆能力和生动形象的汉语言表达能力。中国古典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我自觉也读了不少,但让魏老师叙说出来,确乎是别有一番滋味,备感受益匪浅。正是在魏老师的鼓励和影响之下,我终于开始发表作品,并且渐渐地由少到多,如早期的《沧海》《草儿青草儿黄》《寻驼》《牧歌》《少年和大漠》等,其中就多处引用了魏老师编译的阿拉善民歌。只要我发表了作品,魏老师比谁都高兴,乐得满脸开花,而我也能乘此机会在他那里混一顿酒喝。凡此种种,便是我将魏巴特尔先生称之为文学恩师的由来。
文学,让我们结缘……
同 道
同道,按照一般的解释,即志同道合的人。以我之见,志同者天下比比皆是,道合者未必有多,所谓“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两者之间的不同看似相近,其实是天壤之别,前者谓之君子所为,后者谓之小人之行。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不说也罢。
1991年,阿盟文联正式成立,这对于一帮远离文化中心,在边塞之地舞文弄墨的文朋诗友们而言,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像是离散的游子终于找到了娘家,很有些归宿感的。具体的筹措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魏巴特尔先生的身上,而由他担当文联主席,实在是众望所归。道理其实很简单:非成就斐然且德高望重之人不可,否则难以服众。文联主席内定了,还缺个秘书长,魏老师于是想到了我。考虑到方便我文学创作情况的同时,魏老师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文联必须至少有一名汉族同志,用魏老师的话说是阿盟文联不能办成“蒙古族文联”。他这个人不会虚情假意,不会茫然四顾,更不会虚与委蛇,有啥说啥,绝对性情,在为人处事上是很有些融融古风之意和古道热肠的。征求意见时我心里却非常不安,觉得自己并不般配,但面对魏老师那一双充满真诚、热切和期待的眼睛时,我又不好拒绝。人生得一知己,谈何容易?为了我的调动,魏老师于是开始了他的游走,像一个说客那样来回奔忙。那时交通很不方便,大热的天暑气逼人,魏老师骑着一辆丁当乱响的自行车,满头大汗地在老陵滩和西花园之间穿梭,向旗委领导陈述调我的理由,其言凿凿。后来,时任旗委书记的达来先生找我谈话,询问我个人的态度,我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就差说出“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了。达书记想了想说,你想在这方面(指文学创作)发展也是可以的,人各有志嘛。这事还惊动了时任盟委宣传部长的冯国进先生,意思是老魏执意要调的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一次,我正在伏案写材料,就听办公室主任喊我,去了方知冯部长在座,见了我当即哈哈大笑,继而风趣地说,一个胖乎乎的傻小子嘛,听说你文章写得还不错。接下来,便是一路绿灯。后来听魏老师讲,当时的黄盟长(我的中学老师)在我的调动表上签过字后,语重心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两个老实人走到一起了。
两个老实人。
这话令我思之久长,心情很不平静,对我触动很深。是啊,可不就是两个老实人吗?一语中的。那么,两个老实人走到一起,究竟能做些什么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文联成立之初,条件十分简陋,尤其经费短缺,真正是《百家姓》里缺了第二姓,没有一分钱可以开销。不过,魏老师有办法。他不慌不忙地拉上我,说找财神爷去。那天临近下晚班,魏老师和我去了时任盟财政处长的塔拉腾先生家里,事先没有约定。怎知塔处长家正在招待从牧区来的亲戚喝酒,“两个老实人”想退出去显然是来不及了,只好“既来之,则安之”,大大咧咧地入了席,用魏老师的话说是,我们也做一回亲戚。主人热情,客人更加不好推辞,便放开了吃喝,以致醉得一塌糊涂,趴在桌子上人事不省。等到主人送走亲戚回来又等了许久,“两个老实人”才从梦里渐渐醒转,然后摇摇晃晃地起身告辞。出门时,魏老师和塔处长相视一笑,心知肚明。已经是后半夜了,天上的星星出得齐全,在繁茂如织的星空下,“两个老实人”头重脚轻、磕磕绊绊,一边走一边仰天大笑。过了不几天,魏老师兴冲冲地告诉大家,两万元到账,同时还引用了领袖的一段语录聊以自慰: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应当统筹解决。魏老师的幽默和风趣,由此可见一斑。每逢有魏老师的场合,必定充满了欢声笑语,即使有再多的忧愁,都会在这种场合得到稀释和化解。我是这样认为的,幽默是大智慧,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具备的。幽默折射出来的是心胸的开阔和豁达,是经历了沧桑之后的淡定、从容和超脱。有如一篇好的文章,必定是经历了繁复之后的简单,是清静的,是安然的,甚至是“无为”的。我心目中的魏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从他身上折射出来的人格的力量,感动着他身边许许多多的人。当然,魏老师也有愤怒的时候,对一些看不惯的社会现象也会进行猛烈地抨击,只不过是仍然采取他一贯幽默的方式,听来不仅令人捧腹,而且十分的解气。惜乎,那些精彩的段子是不能录在这里的,只能靠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接下来,在魏老师的提倡下,文联用这两万元经费与《草原》编辑部共同举办了颇有声势和规模的文学笔会,并就近邀请了宁夏文联《朔方》的编辑人员,为阿盟的文学创作者举办了一次文学的盛宴,促成了《草原》阿盟作者专号,让三十四位用汉语写作的阿盟作者集体亮相。应该说,此举对当时显得有些沉闷的阿盟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在阿盟的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尽管其中的一篇小说《沙暴》因为所谓的“人性异化”引起过不小的争议。作为编辑之一,我深知其中的内情,为了让更多的作者能够“抛头露面”,魏老师坚决撤掉了自己的中篇小说《身边的遥远》。《草原》的责任编辑白雪林先生不无遗憾地表示,就其质量而言,《身边的遥远》无疑是这一期专号的头条。时隔多年之后,当我读到魏老师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天河》时,油然而生感慨:《身边的遥远》实在不应该就那样被无声无息地埋没。
哦,身边的遥远……
牵 挂
1995年5月,我做出了一个让阿盟的文朋诗友们认为不可思议的举动,去向宁夏的银川市。究其原因,同样与魏巴特尔先生不无关系。魏老师先我离开阿盟文联去了政协,他的离开,使我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境地,那一时期我的情绪很低落。尽管文联的其他同志一如既往地对我很友善,可我还是觉得自己像孤家寡人,也许是“两个老实人”交情太深,工作中相互配合得太默契的缘故吧。惺惺相惜,实属人之常情。说句实话,我之所以这样做,其中也有和魏老师赌气的成分在里面:你走我也走。谁知道,我这一走就再也回不去了。
虽然只是一山之隔,直线距离不过百公里,但毕竟是横跨两个省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我又必须在新的地方和新的环境里全力打拼,和魏老师的往来无法避免地少了。当然,我们有一点是共同的也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是在为“稻粮谋”的同时,还在继续文学创作,仍然坚守着文学的精神和理想。到宁夏的前些年,每逢春节的时候,我还是要去魏老师家的,去了必定有一番长谈,相互通报各自的创作情况,佐以好烟好酒,更不乏欢声笑语。在亲朋好友娶媳妇嫁女儿的宴席上,以及几次阿盟文学界的会议上,在主人的刻意安排下,我都和魏老师同桌同台。记得在贺兰山南寺举办的一次文学采风活动中,魏老师就当着大家的面,首先拿我开涮,狠狠地幽默了一把。意思是说,阿拉善的骆驼都是双峰驼,而且驼峰都长在后面的脊背上,可是有一峰“骆驼”却很奇怪,不仅驼峰是单的,更糟糕的是驼峰长在了前面的肚皮上。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峰“骆驼”离开了阿拉善,从山后跑到山前吃人家的大米去了。此言即出,满堂哄笑,气氛是再好不过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经典的段子,其中就有大智慧,耐人寻味。我在这篇文章里将此呈现出来,有与读者分享的意思。这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将欢乐带给别人的人,和魏老师这样的人在一起,绝对是人生中的大幸运,天会格外地高远,地会格外地辽阔,阳光会格外地明亮,风儿会格外地清爽,人间会格外地温暖和美好。
也真是让魏老师言中了,在宁夏的青年作家群里,他们还真的是毫不客气地,同时也是没有任何恶意地给我起了个“老骆驼”这样的绰号,我便也很情愿地接受了,内心里还挺愉快和自豪。他们之所以称我为“老骆驼”,原因大概有这样几条,一是我本来就来自于中国的骆驼之乡阿拉善;二是我创作发表的很多作品都写了骆驼,譬如《老满最后的春天》《夜走十三道梁》《父亲与驼》《失驼》《冬日》等;三是就我的慢腾腾的性格而言,也像一峰负重远行的骆驼。这样岂不更好?这样就使得我的文学创作及其作品和他们区别开来,不和他们“靠色”。我在一篇创作谈里说过这样的话,出生地和儿时的经历,尤其对作家和诗人很重要,决定着写作的情感因素和精神向度。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至今发表的百余万字的小说作品,无一不是叙写阿拉善的。没有阿拉善就没有我的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穿插这样一段文字,意思是想告诉魏老师的在天之灵: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不会有所谓的“下一个精神故乡”。正如作家石舒清所言,写作就是写自己,写自己的经验和认识,写自己的性情和主张,而这一切首先是建立在故乡之上的。
我们不仅仅共同地坚守着一种文学的精神和理想,“两个老实人”还彼此之间深深地牵挂,有时候竟然成为了积淀在心里的一种沉重,浓得化不开。
记得《阿拉善报》创刊二十周年社庆那次,我因采访任务去了泾源县,《朔方》编辑部便委派诗人杨梓和梦也到阿拉善报社参加庆祝活动,宴会时他们恰好与魏老师同桌。当魏老师得知他们二人和我是同事,便一再追问我的情况,惦念之情溢于言表,反复问我的处境怎么样?文联领导对我好不好?主编对我好不好?同事们对我好不好?随后又拉着他们的手一再叮嘱说,那是一个老实人,你们一定要互相团结,平时多帮助他。直到我的两位同事也一再表态,做了肯定的答复,最后几近于举手发誓,魏老师才放下心来,开始开怀畅饮。两位同事回到编辑部后,向我仔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然后困惑地说,那个魏老师和你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对你的关切和担心的程度,似乎远远地超出了朋友的范围,即便是亲兄弟也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其实,他们在描述那样的情景时,我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觉得自己当时就坐在魏老师的身边。我向两位同事讲了我和魏老师之间很深的那种情意后,他们也是感叹唏嘘不已。当我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我就会觉得这样的牵挂是不是显得沉重了些?沉重得让我有些承受不起。不过,在很多的时候,它也会成为一种动力,激励和鞭策着我,既然是一峰负重的“骆驼”,就应该有骆驼的那种坚韧和耐力,不怕慢就怕站。魏老师当初的担心不无道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预言。我是个不设防的人,在这个并非人人从善如流的社会环境里,老实人吃亏是难免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莫名其妙地陷入了人事的漩涡中,在个别人的攻击和造谣伤害中差一点离开编辑部。正是在那一段处境极为艰难的时期,我是那么的怀念和魏老师曾经相处的美好日子。当然,我还是坚持了下来,谣言最后不攻自破。我也深知,这其中就有魏老师那真诚而又显得沉重的牵挂,在不断地激励着我,在不断地鞭策着我,使我不敢也不能有丝毫懈怠。
我家住老城,前几年从阿盟文化馆调入北方民族大学(原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的画家朝戈巴图家住新市区,我们两个人每逢见面,魏老师是我们久谈不衰的话题,而且越往下谈越深入。有一次我说,魏老师是一个具备了神性的人,他的人格魅力无几人可比。情到深处,再加上酒兴所致,朝戈巴图便给我讲了有关魏老师的许多经历和故事,其中的大部分我也是知道的,曾经听魏老师自己和别的人说起过,例如骑在驼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背《新华字典》、两座蒙古包那么多的书被造反派付之一炬等。但有些我是第一次听朝戈巴图说,尤其是魏老师在“文革”中遭受的种种磨难和屈辱,那真是非常人能够忍受得了的(也惜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道出)。就这样,栖居银川的分属不同民族的两个阿拉善人,在酒桌上说的却是同一个家乡人,这个人就是大善大德、大慈大悲的具有苍天般的情怀的魏巴特尔先生,我们文学、艺术、人生的师长和楷模。
后来,魏老师退休了。我和退了休的魏老师有过几次见面和交谈。那时的魏老师,身体依然健朗(稍微有点发福,也多了几许白发),酒量似乎也不减当年,依然是那样地幽默和风趣。他告诉我说,退休后的感觉不错,每月两千多元的退休工资,足够了。魏老师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知足常乐,用在这样的人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然后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说是闲了其实更忙,欠了不少文债,手里的活计不断,有很多相关的文史资料需要他搜集、整理和翻译,多家出版社都“等米下锅”呢。魏老师还有一个庞大的个人创作计划,除了创作小说之外,还要续写《红楼梦》和《水浒传》,而且是蒙文和汉文同时进行(他早就告诉过我,而且我还有幸读到过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一开始是很惊异的,惊异之余便是佩服,用五体投地来比喻也并不为过的。能够同时在现实题材和古典题材两个领域里大显身手、游刃有余,除了大气魄,还要有大手笔。对此,我没有产生一丝怀疑,后来的事实也是有所证明的,《阿拉善传说》和《天河》应该就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吧。《阿拉善传说》共七十二回近二十万字,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大约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正如本书前言指出的那样,是一部传说化的阿拉善历史或者阿拉善历史的艺术记录,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此书不可不读,尤其是阿拉善人不可不读。作为从业多年的文学编辑,我也叹服这部作品语言的流畅和通泰,以及掩藏在文字里的具有“魏氏风格”的智性和趣味。遗憾的是,魏老师的很多作品是直接用蒙文写作和出版的,没有来得及翻译成汉文出版,譬如他的长篇小说《晦暗岁月》等,于我只能是两眼抹黑了。
要说我对魏老师有什么牵挂,这就是了,是牵挂和期待他的作品能够尽早问世和更多问世,让我一读为快,分享恩师的硕果和喜悦……
别 离
我实在不忍心写下这一章,可又不能不写。不写,我就无法原谅自己、说服自己。
后来,就听说魏老师生病了,而且是大病,是李亚玲女士首先告诉我的。她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十分不祥的消息的时候,言语中包含了对我的幽怨和指责,意思是魏老师对你那么好,他病了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不来看望?令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我知道我是不能做任何解释的,尽管我是真的不知道,可以这样说,打死我都想不到。等放下电话,我一时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脑袋像是在无极限地膨胀着。不久前,魏老师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还结结实实地喝过一场酒呢,魏老师照例妙语连珠,酒桌上照例欢声四起。之后又约定由魏老师亲自带队,几个要好的朋友在银川再聚,他们要对我进行一番实地“考察”。而我也是做好了准备的,向几个在银川工作的阿盟籍的朋友打了招呼,其中就包括画家朝戈巴图。
怎知道等来的却是坏消息。怀着深深的愧疚,我去看望魏老师,我不敢想象魏老师被巨大的病痛折磨成了什么模样,他曾经是那么豁达和开朗、那么幽默和风趣的一个人啊。魏老师瘦了,瘦得很厉害,但精神看上去还不错,见了我显得特别高兴,又说又笑的,可我怎么也笑不出来,一时语塞继而哽咽,心情极其复杂。随着情绪逐渐平静下来,我和魏老师聊了大约有一个小时,便起身告辞,主要是担心时间长了魏老师身体受不了。令我惊叹的是,在和我聊天的过程中,魏老师像往常那样神态自如,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知道了我的疑虑后,魏老师若无其事地反过来安慰我说,不怕,我不坚强谁坚强?后来,我几次要去再看望魏老师,都因为说是魏老师外出治病而未能如愿(我甚至怀疑这是魏老师善意的拒绝)。
我不坚强谁坚强?这是魏老师给我说下的最后一句话。
我不坚强谁坚强?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7月7日,我的文学恩师、敬爱的魏巴特尔先生走完了他朴实而厚重、平凡而高尚的一生。先生走的时候,执意只穿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衣服,带着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先生毕生珍爱的《普希金诗选》。写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再也写不下去了,泪眼迷蒙中,我想起了这样一首诗:风从草原上吹过,一个骑马人向天边跑去。不过,面对一个伟大的灵魂,我更愿意借用先生自己编译的一首阿拉善民歌为先生祈祷:
富饶辽阔的阿拉善
是我们难得的故乡
漫漫香火是虔诚的信仰
太平美满是我佛的祥光……
200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