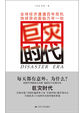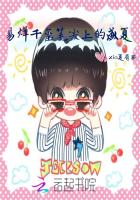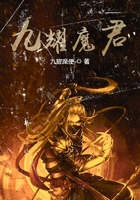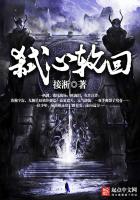第三节 周王朝的强盛和衰落
代殷而起的周王朝是我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繁荣鼎盛的时期之一。从公元前11世纪周灭殷开始,到公元前249年周王朝的残余势力最终被秦灭掉,周王朝绵亘于我国上古历史达八百余年之久。虽然自周平王迁东洛邑以后周王朝的势力日趋没落,但其典章制度、思想文化却依然有着巨大影响。
一、周族的起源
周族历史悠久,一般认为它兴起于“陶唐、虞、夏之际”(《史记·周本纪》)。相传周的始祖弃曾被舜命为“后稷”,“播时百谷”(《尚书·尧典》),并和大禹一起治水(《史记·夏本纪》)。关于周族兴起的时代,没有什么大的疑问,专家们争论较多的是周族起源的地域问题。
关于姬周族【88】的最初居地,学者们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不少人认为是在今陕西的泾渭流域。其主要根据有三项:一、《诗经·生民》谓后稷“即有邰家室”,邰地在今陕西武功县。二、与姬周族累世婚姻的姜族自来居于关中平原西部,传说宝鸡一带有姜太公垂钓处姜城堡、神农祠等。三、考古资料表明,关中地区的漆水下游有不少先周文化遗址,可见先周文化是一种土著文化。
和这种说法不同的是姬周族源于今晋境说。首倡此说的是钱穆先生【89】,后来吕思勉【90】、陈梦家【91】两先生陆续采用钱说。从考古学角度对此说加以说明的有邹衡【92】、李仲立【93】两先生。近年,王玉哲、李民两先生又从新的角度对此说加以证实。【94】诸家所论虽然大旨不误,亦多有发明,但因侧重点不同,故而详略取舍各自有别。总括诸家所论,经梳理补充并稍加修正,可以对姬周族源于今晋境说提出下述几项比较系统的论证。
第一,先周历史上屡有邠称。如《孟子·梁惠王下》谓“昔者大王居邠”,《逸周书·度邑》谓“王乃升汾(《周本纪》引为豳)之阜,以望商邑”等。由于邠、豳同字【95】,所以又屡有豳称。如《诗经·公刘》谓“于豳斯馆”,《史记·匈奴列传》谓公刘“邑于豳”,《史记·周本纪》谓庆节“国于豳”。姬周族以邻相称,应当是由于它长期居于汾水流域的缘故。周厉王曾经避难到汾水边上的彘邑居住十四年之久,以至《诗经·韩奕》称他为“汾王”。周宣王败于姜戎氏以后曾经“料民于太原”(《国语·周语上》)。这些都说明汾水流域是姬周族的根基之地。后来公亶父迁岐时才将邠称带了过去,犹殷人所居之地皆称亳然。
第二,《诗经·绵》追述姬周族发祥史说:“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此“土”应当和《诗经·长发》“禹敷下土方”之“土方”以及殷墟卜辞习见的“土方”有关系。或谓土方即《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唐杜氏”之杜,或谓它在今山西石楼一带,其地望均在今晋境。《诗经·公刘》有“逝彼百泉”、“观其流泉”之句,与今晋境泉水特多的情况相合。《水经注》卷四谓:“水出汾阴县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开源,喷泉上涌,大几如轮。”陈梦家说:“此所形容,当是今万泉县东谷中有井泉百余区之地。”【96】此地在今晋西南,公刘所视之泉,当即此处。
第三,公亶父自邠迁岐时,其子“大伯不从”(《左传》僖公五年),仍留在姬周族原住地,做了虞国始祖。虞在今山西平陆境。此可证迁岐以前姬周族必在今晋境,故而《穆天子传》才说“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虞)”。如果说姬周族源于泾渭流域,那就不会有“西土”、“东吴(虞)”的说法。《尚书·大诰》云:“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此称泾渭流域为“西土”,则其“东土”即当指汾水流域。公亶父迁岐的原因,或谓“狄入侵之”(《左传》僖公五年),或谓“薰育戎狄攻之”(《史记·周本纪》)所谓“狄人”、“薰育戎狄”,皆古有易族的名称。有易族原居于今冀境的易水流域,后被商族攻击,“昏微遵迹,有狄(易)不宁”(《天问》),被迫西迁,而与居于汾水流域的姬周族冲突。经过长时期的相持斗争,姬周族也被迫西迁。依今晋冀接壤的形势观之,姬周族也应是居于今晋境,而不会在今陕地的。
第四,周人屡次自称“有夏”,如“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君奭》)、“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尚书·立政》)等皆然。姬周族和夏关系密切,甚至可能原为夏族分支。《逸周书·商誓》:“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迹。”这里明确指出后稷活动于“禹之迹”。《尚书·康诰》篇谓文王“用肇造我区夏”。夏的基地在今豫西、晋南一带,这屡为考古和文献资料所证明。《诗经·閟宫》说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谓后稷所居为禹之故地。《閟宫》还说“实维大王,居岐之阳”,明确指出迁岐自大(太)王始。从姬周族与夏的密切关系看,姬周族也当在今晋境而不在今陕地。春秋时人叙述周族发祥史,谓自夏世至武王克商以前曾据有魏、骀、芮、岐、毕五地,前三地中的魏、芮可确知为今晋境之地,其中间的骀亦当如此。这里所述五地,前三处在今晋,后两处在今陕,可见在春秋时人的印象里,周人是由今晋境而至今陕地的。(《左传》昭公九年)
第五,后稷母姜原是有邰氏女。《路史·后纪》卷三:“上妃有邰氏曰姜原。”有邰氏当即《左传》昭公元年所谓的“封之汾川”,后来又成为“汾神”的台邰氏。既然被封在汾川,那么其地望亦必在今晋境,后稷的“即有邰家室”(《诗经·生民》)也当在今晋境。
第六,与姬周族累世婚姻的姜族多居于今晋境。姜族最著名者有齐、许、申、吕四国,古称“四岳”(《国语·周语下》)或“太岳”(《左传》隐公十一年、庄公二十二年)。《诗经·崧高》谓“维岳降神,生甫(吕)及申”,即明指姜姓的甫(吕)、申与“岳”有直接关系。春秋时代的姜戎氏曾经自称“四岳之裔胄”(《左传》襄公十四年)。四岳、太岳古均指今晋境的霍太山,因此与四岳、太岳有直接关系的姜族应当是在今晋境的。姜与羌古同字。卜辞关于羌的记载有近万条之多。羌族在卜辞里又分为“马羌”(《合集》6624)、“北羌”(《合集》6628)、“羌方”(《合集》22982)、“丹黾羌”(《合集》451)等部,多居于今晋境。尽管今陕西和甘肃南部也有姜族分布。但其主要居留地仍在今晋境,这就为姬周族源于今晋境说提供了一项旁证。
第七,考古材料也证明姬周族源于今晋境。先周墓葬,不论大小,一般都随葬陶鬲。常见到的只有分裆鬲和联裆鬲两种。其联裆鬲的形制恰与山西光社文化的相同。“由于光社文化的这种联裆鬲的年代比先周文化第一期要早,因此只有一种可能,即先周文化的联裆鬲是从光社文化来的,而绝对不可能相反。”【97】另外,姬周族里有徽号作铜弓形的和作“天”字形的两个著名氏族,根据对所出土的这两个氏族的百余件铜器的断代和分布区域的研究,邹衡先生指出,这两个氏族早期居于今山西,后迁至今陕西的泾渭流域,克商以后,有的支族才迁至河南。【98】不难发现,这个论断是姬周族源于今晋境说的极有力的证据。
总之,和姬周族源于今陕西泾渭流域的说法比较起来,姬周族源于今晋境说的证据比较充分,应属可信。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上古诸族屡有迁徙,因此相关的地名和史迹也往往随之带到各地,例如商亳就有四五处之多。泾渭流域是公亶父以后的姬周族的根据地,在这些地方出现先周的某些地名和史迹并不能说明姬周族源于泾渭流域,而只能窥见姬周族自今晋迁陕的某些源流发展情况。
关于姬周族国号问题,古代的学问家多有所论。最早的可能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他说:
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史记·匈奴列传》,索隐谓“作周”即“始作周国”)
东汉时期的高诱说:
岐山之阳有周地,及受命,因为天下号也。(《吕氏春秋·古乐》注)
高诱认为周的称号源于岐山之阳的周地。魏晋时期的皇甫谧进一步指出:
公亶父“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史记·周本纪》集解引)
他断定周称自公亶父始,并谓“始改国曰周”,可见,皇甫氏以为公亶父以前并不称为周。唐朝的张守节明确指出:
因太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史记·周本纪》正义引)
唐朝的司马贞也说:
后稷居邰,太王作周。(《史记·周本纪》索隐述赞)
“太王”即公亶父,司马贞也认为周称自公亶父起。但公亶父以前的周先王在文献中也偶有冠以周称者,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谓“周弃亦为稷”,对此,唐孔颖达解释说:
弃为周之始祖……以其后世有天下,号国曰周,故以周冠弃,弃时未称周也。(《春秋左传正义》)
总之,古代的学问家多以为周称始于公亶父,因周原的地名而称之。
那么,在公亶父以前,姬周族的国号是什么呢?上古的国号、族号往往因地名而起,“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国语·晋语》),就是著名的例证。准此原则,姬周族最初的国号并不难弄清。
既然姬周族最初居于今晋境的汾水流域,那么,因地而命名,则其国号当为汾,或是与汾音相同的邻若豳,而不称为周。请先看《今本纪年》的以下记载:
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
盘庚十九年,命邠侯亚圉。
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组绀。
武乙元年,邠迁于岐周。
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
高圉、亚圉是公亶父以前的姬周族的著名首领。《国语·鲁语上》:“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左传》昭公七年载卫襄公卒,周王遣使吊唁,其辞有云:“余敢忘高圉、亚圉?”疑卫祖与高圉、亚圉之后裔有关。《今本纪年》提到的组绀即《周本纪》的“公叔祖类”、《世本》的“组绀诸盩”。从《今本纪年》的记载里可以看到,古公以前的组绀、亚圉、高圉等皆称“邠侯”,迁于岐周后才冠以“周”称。这是对姬周族国号起源问题的很好的说明。
《今本纪年》的这些记载可靠吗?
尽管《今本纪年》的问题很多,但是其中不少内容是从类书、古注里摘引的,据推测它的出现“最迟当在南宋时期”,其编纂者所见到的《古本纪年》佚文“可能比我们看到的为多”,所以,“仍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99】。杨树达先生也曾指出《今本纪年》“大都有所据依,非出臆撰”【100】。王国维著《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以“捕盗者之获得真赃”(该书序言)的办法追寻《今本纪年》剿袭它书的证据,但对邠侯的记载却不能置一词,可见这个记载应当是可信的。《今本纪年》关于邠侯的记载可与古本相互补充。《古本纪年》的《殷纪》里,武乙以前缺周事,《文选·典引》注引“《纪年》曰:武乙继位,周王季命为殷牧师”为古本提及周事之最早者,今本关于邠侯之载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缺。另外,从世系上看,殷祖乙至武乙间有六世,而《周本纪》所载高圉至公亶父间仅两世,《今本纪年》的排列似有可疑处。历代学者根据《山海经》、《路史》等记载,多认为周代世系必有“失其代数”(《史记·周本纪》索隐)者,根据文献记载,高圉至古公间至少可以拟补两世,所以《今本纪年》关于邠侯世系的记载当属可信,尽管其系年未必准确,但其大旨是可靠的。
既然姬周族源于今晋境,在公亶父以前长期居于汾水流域,既然高圉等被称之为邠侯,那么,姬周族所立国在公亶父以前应当是称为邠或汾的。《尔雅·释地》:“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说文》引“尔雅”作“汃国”。《说文》平字下谓“从八。八,分也”,半字下谓“半,物中分也。从八从牛,牛为物大,可以分也”,《说文》训分、八皆为“别也”。凡此皆可证八与分相通。因此,汃当与汾同。此“邻国”指极西地之国,应即姬周族居汾水流域时所建立的国家。它给上古时代的人留下深刻印象,陈陈相因而为《尔雅》所采。因为邠通于豳,所以《周礼·春官》注引郑司农说又称“豳国之地”。《说文》:“邠,周大王国。”按,此说稍有误,应谓邠指周大(太)王迁岐前之国。《史记·周本纪》:“庆节立,国于豳。”显而易见,这些文献记载也为姬周族的国号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殷墟卜辞里关于“汾方”、“侯汾”的记载。这些不仅能和文献记载印证,而且是姬周族国号问题的最直接的证据。甲骨文有“分”字,《甲骨文编》和《甲骨文字集释》都释为分,可信。在卜辞里,“分”用为地名,应与汾同。甲骨文有从水从刀之字,诸家漏释。以刀为偏旁的甲骨文多有分割义,如利、剢、黎、初等皆然。《说文》:“分,别也,从八、刀。刀,以分别物也。”这个字从以刀划水取义,当是汾字初文。和这两字相关的卜辞有:
(1)甲申卜贞,我弗其受分(汾)〔方又〕【101】(《合集》9728)
(2)弗(?)载汾。(《合集》6660)
(3)(?)汾方。(《合集》6659)
(4)……巳卜贞,以侯汾。(《合集》9154)
(5)癸酉卜,疋于栗……汾从。(《合集》19956)
(6)……分(汾)养(牧)。(《合集》11398)
(7)癸未卜,兔以汾人,允来。(《屯南》427)
(8)……驱分(汾)人。(《合集》31997)
上引(5)为(?)组卜辞,(7)、(8)为第四期卜辞,余皆第一期卜辞。上引前三条卜辞贞问讨伐汾方能否受到神灵保佑。(4)辞的“侯汾”即汾侯,犹“侯告”即告侯、“侯专”即专侯者然。这条卜辞贞问是否征召汾侯。《今本纪年》载盘庚时曾“命邠侯亚圉”,依时代而论,(4)辞的“侯汾”有可能是邠侯亚圉。(5)辞贞问名疋者驻军于栗,入于某地时是否让汾跟从。此汾盖指随王室军队征伐的汾侯的族众。(6)辞的养字原从羊从殳,罗振玉释其为牧,李孝定根据它与《说文》所载养字的古文合而释为养字,谓它“像手执杖以驱羊,与牧同意”(《甲骨文字集释》卷五,1770页)。这条卜辞贞问是否于分(汾)地放牧。卜辞有“于南养(牧)”(《合集》11395)、“养(牧)于唐”(《合集》1309)等,皆与(6)辞同例。(7)辞贞问名兔者征召汾人能否来到。(8)辞同版有关于父乙的贞问,第四期卜辞的父乙即武乙,所以这条卜辞属文丁时期。这条卜辞贞问驱逐分(汾)人之事。
分析上引卜辞所载,有下述各事值得重视:
第一,文献所载殷周关系,其时代最早者为祖乙“命邠侯高圉”(《今本纪年》)。这时殷的别都在今冀南邢台一带,与姬周族所居的今晋南相邻,此时殷周间有了初步关系是十分可能的。但武丁时的殷周关系,文献阙如,上引第一期卜辞正补文献之阙。
第二,在武丁初期,汾曾经是殷的敌国,上引(1)至(3)辞关于讨伐汾方的记载可为其证。
第三,在武丁后期,经过讨伐,汾即宾服。此后殷周关系渐趋密切,卜辞有征召“侯汾”、“汾人”和“汾从”的记载,这与盘庚、祖甲时“命邠侯”(《今本纪年》)的文献记载完全一致。《古本纪年》屡载季历伐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而受到武乙赏赐。卜辞极少有称某方又称某侯之例,然而却有“汾方”、“侯汾”之载。这些都表明了殷周关系的密切程度。
第四,(7)辞表明,汾地曾为殷的放牧处。姬周族强大以后,武乙曾命季历为“殷牧师”(《古本纪年》)。对此,卜辞和文献所载亦相合。
第五,文丁时期姬周族虽已迁于岐,但仍讨伐今晋境的余无、始乎、翳徒诸戎并皆大捷,可见姬周以岐为基地将势力又扩展至今晋境。在殷商感到威胁、无可容忍的时候,终于导致“文丁杀季历”(《古本纪年》)。文丁此举,意在夺取今晋境。上引(8)辞就是文丁驱逐汾人以控制今晋境的记载。
姬周族迁岐以前称为邠或汾,通过对相关文献和卜辞记载的考察,这种说法应当是可信的。此外,我们还可以提出一项佐证,那就是在周人的史诗和谕诰文献里,其自称为“周”总是从公亶父开始,而追述公亶父以前的历史时却从来不用“周”称。他们认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文王》)。什么时候开始受命为周了呢?《诗经·下武》说:
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他们认为武功强盛的周邦自来有圣哲之王——即已经升天的“三后”和正在京师执行帝命的武王。“三后”指太王、王季、文王。这几句诗确凿地说明周称自太王(公亶父)起。《史记·鲁周公世家》载东征以前周公语:“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称周之先王亦从太王起。《尚书·无逸》载周公语“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金縢》谓太王、王季、文王为三王,皆其例。周人有时也称“二后”(《诗经·昊天有成命》),指文王、武王。《逸周书·世俘》载武王灭商以后至周庙告祭“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所列周先王亦自太王始。如果自来就有周称,那么后稷、公刘、高圉、亚圉便不至于被完全排除在周先王以外。《生民》、《公刘》是追述姬周族史迹的长篇史诗,两诗中均不见“周”字,讲后稷只谓“即有邰家室”。讲公刘只谓“豳居允荒”,无一处提及后稷或公刘时已经有了周称者。从周人对自己的历史的追述看,确是从太王时始有周称的。皇甫谧所谓公亶父迁居岐“改国曰周”的说法,有此为证,可谓信然。
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皇甫谧所谓公亶父“邑于周地”之说是否正确,即周原之称是古已有之,抑或是公亶父带来的地名。《诗经·绵》云: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膴膴,堇茶如饴。
古公到岐,见到“周原膴膴”,是周原之称必在公亶父迁来以前。《路史·国名纪》卷一云:
郮,《潜夫论》:詹、资、郮、翟,黄帝后。故《玉篇》云:资、郮故国,黄帝后,封在岐山之阳,所谓“周原膴膴”者,顾伯邶云:昌意后,止于夏商间。罗泌所见《玉篇》当系别本,《玉篇》通作“郮,故国。黄帝后所封也”,与罗氏所引大旨相同。不管郮是黄帝后,或是昌意后,既然其“止于夏商间”,那么它的时代必远在古公迁岐称周以前。很可能夏商之时在周原居有黄帝部族的某一支系并以周为称,后人加邑旁称为“郮”。《诗经·绵》谓公亶父迁岐,“行道兑矣,混夷駾矣”。此混夷即原居于岐下者。混夷,《诗经·皇矣》作串夷,《汉书·匈奴传》作畎夷,属于犬戎之一支。《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它是黄帝后裔,可见其为姬姓。这与作为“黄帝后”的郮是一致的,很可能岐地原有的郮国即为混夷所立。陕西扶风的柿坡,岐山和扶风交界处的樊村、召陈、任家、康家、庄白、齐镇、方塘、齐家、礼树、贺家、董家、王家咀等处都发现有早周遗址,有些遗址的时代早于周原遗址,这些情况都说明公亶父来此以前,周原一带并非荒无人烟之处,而当有先民——很可能就是后来被称为“郮”的一支姬姓部族居于此处。周原之称“周”应在公亶父迁岐之前,皇甫谧关于公亶父“邑于周地”而改称为周的说法,亦可谓信然。
总之,姬周族所立国的称号前后有所变化。它居于今晋境时,因汾水而得名,称为汾或邠【102】;公亶父迁岐后因邑于周地而改称为周。姬周族国号演变的荦荦大端是信而有征不难发现的。
二、商周关系问题
殷墟卜辞里载有关于“周”的卜辞,论者多以之为据而探讨商周关系问题。这对于研究周族的兴起至关重要,值得我们单独提出来进行分析,以便对于商周关系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如果姬周族在太王以前居于今晋境并且以汾(邠)相称的说法可信的话,那么人们便会很自然地考虑到如何理解殷墟卜辞里的“周”的问题。旧说认为殷墟卜辞里的“周”就是夏商周之周,亦即姬周族之周。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关键在于忽略了殷墟卜辞里的“周”的特定的含义。
甲骨文周字初皆误为卤字,释为鲁。后来孙诒让、吴大澂等经过对甲骨文、金文的比较研究,始释为周字。诸家从之,终成定论。释“周”之说,大旨不错,然其造字本义和音读起源仍然不明,这样也就严重影响了相关卜辞的理解。
古代文献里,周与舟每相通谐。如《诗经·大东》:“舟人之子,熊罴是裘。”郑笺:“舟当作周。”《考工记》:“车行以陆,作舟以行水。”郑注:“故书舟作周。”屈原《九歌》:“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尚书大传·虞夏》:“舟张辟雍,鸧鸧相从。”《尔雅·释训》:“侜张,诳也。”所云“周章”、“舟张”、“侜张”与汉魏以降的“倜傥”,实皆一词。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舟写作“周”。《左传》宣公十四年的“申舟”,《吕览·行论》高注作“申周”。《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的“华周”,《说苑·立节》作“华舟”。《说文》的“(?)”俗作週,《尔雅·释训》侜字《释文》谓“或作倜”。均为周、舟相通之证。《诗经·河广》“曾不容刀”,郑笺和《释文》均谓“《说文》作(?)”。今本《说文》无(?)字,段玉裁据之以补。《释名·释船》:“三百斛曰(?)。”(?)字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周”的本义隐晦是比较早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周”的本义确实为桴(舟),(?)字以舟为偏旁,是对“周”的本义的强调。周与舟相通谐,不仅由于其古音相同,而且由于它们在造字本义上同出一源。
据《安阳县志》记载,在安阳西北四十里有铜山,曾产过铜。安阳以西的水冶,以南的汤阴高村桥一带现在还产铜。今安阳后冈西南不远的铁路苗圃北地是殷代铸铜作坊遗址【103】,距洹河甚近。在小屯村和高楼庄、薛家庄南地也发现了数处铸铜遗址。【104】这些遗址都在洹河南岸的近处。殷代航运业甚为发达,卜辞屡有这方面的记载。盘庚迁殷时,曾涉大河,并以“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尚书·盘庚》)作比喻。另外,殷代青铜铸造业高度发展,不仅青铜器的数量巨多,而且多厚重古朴的重器。这样看来,所需铜矿石的数量一定是十分可观的。根据上述情况分析,如果说为了满足铸铜业的需要,殷人从殷墟周围的某地开采矿石,然后沿洹河等以桴(舟)运至铸铜作坊,这应当是完全可能的。
一曰石似玉,从玉,周声。”虽然在经传中琱多通作彫雕用其治玉之义但说文保存了石似玉的训释,这是很可宝贵的。这种“似玉”之石与作为冶铜主要原料的孔雀石十分相似。据研究,“铜矿砂分自然铜、氧化铜和硫化铜三种,硫化铜最难提炼。商代大概用自然铜和氧化铜。在殷墟发现的铜矿砂,都属孔雀石,为氧化铜的一种。其中最大的一块重18.8公斤。这种孔雀石应该就是用以炼铜的矿砂”【105】。自然铜的含铜量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孔雀石的含铜量在百分之七十以上,用以冶铸是十分理想的原料。孔雀石一般呈绿色,有玻璃光泽或金刚光泽,可以琢磨为装饰品。它与《说文》所谓“石似玉”的琱完全吻合。殷代应该称孔雀石和其他铜矿石为“周”的,殷以后,“周”的本义渐隐,古人才又加玉旁造出“琱”字,仍表示“周”字本义。在金文里周与琱通,如《函皇父鼎》的“周?”,簋作“琱?”即为其例。以周为偏旁的画字或从周(《师兑簋》),或从琱(《录伯簋》)。这些都反映出琱所表示的是周之本义。由于琱可琢磨为装饰品,故而琱又引申指彫或雕,“周”的本义遂湮没。
甲骨文周(琱)是个形声字,它以点状表其形,以桴(舟)表其音。在卜辞里,周(琱)绝大部分属于第一期。只偶见于武丁以后的卜辞。殷墟卜辞的所有周(琱)字都不指姬周方国。这可以从两方面证明:一是,卜辞中一部分周(琱)字指铜矿石或玉石制品而言,并非方国名称;一是,卜辞中另一部分作人名、族名、地名的周(琱)字亦非姬周方国名称。兹将这两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分述如下:首先,卜辞里的周(琱)指铜矿石,其确切证据就是关于“凿周(琱)”的记载。
甲骨文“凿”字,为双手持工具在山下开凿玉石之形。因其太繁琐,故而有省写者(《合集》6819、6823、8466)。这个字,诸家多释为寇,为讨伐义,又进而推论“寇周”即伐周,但验之以卜辞文义,均难通读。叶玉森释其为凿【106】,较为合适。在卜辞里,凿字恒与周(琱)连用,如:
(1)己卯卜(?)贞,令多子族从犬侯凿周(琱)古王事。五月。(《合集》6812)
(2)贞,令多子族暨犬侯凿周(琱)古王事。(《合集》6813)
(3)癸未卜争贞,令(?)以多子族凿周(琱)古王事。(《合集》6814)这几例都是第一期卜辞,贞问是否命令多子族、犬侯等去凿周(琱)以执行王事。关于“古王事”的卜辞多不确指何事,明言何事者以“凿周(琱)古王事”为最著,此外仅见两例(《合集》22、5483)将垦田、田猎与“古王事”相关联者。关于征伐的卜辞有数千例之多,无一与“古王事”相关者,而关于“凿周(琱)”的卜辞却绝大部分和“古王事”相关联。我们根据“凿周(琱)”的本义及其和“古王事”相关联的情况,可以断定“凿周(琱)”绝非伐周之义。对此,我们还可以提出这样一项反证,即数千例讨伐卜辞里无一例以“凿”表示讨伐之义者。如果“凿周(琱)”指伐周,那么卜辞里当有“凿土方”、“凿羌方”之类的记载,然而卜辞里“凿”只与周(琱)连用,而不见其他用例。“凿周(琱)”非伐周,此亦为确证。既然甲骨文凿为开凿义,既然甲骨文周(琱)指铜矿石或玉石制品,既然卜辞“凿周(琱)”非伐周,那么关于“凿周(琱)”的合理解释便只能是开采石料。
除了“凿周(琱)”之外,在卜辞里,周(琱)字用其本义者还有作为赏赐物品名称的“周(琱)宓”(《合集》4885、4886)。我认为“周(琱)宓”即“琱柲”。周代金文罗列赏赐物品,其中常有“戈琱(?)缟必彤沙”,盖指以琱装饰之戈。《左传》昭公十二年:“君王命剥圭以为槭柲”,卜辞“周(琱)宓(柲)”应是装饰着圭玉的戈或斧。
其次,卜辞里用作人名、族名、地名的周(琱)字并不是姬周族或姬周之国,甚至不是一个方国名称。这是因为:第一,卜辞有“周(琱)入”若干龟版的记载(《合集》3183反面)。卜辞所说贡纳龟版者皆为殷王朝的头面人物和王室成员及王妇,而从来没有某方国进献龟版的事例。“周(琱)入”的记载表明它不当是方国名称。第二,卜辞有“周(琱)以”(《合集》5654)——即周送诣某种人牲或物品的记载,而卜辞中从来没有某方国主动地“以”——送诣人牲或物品的记载。第三,卜辞中没有称周(琱)为方的辞例。这个字在卜辞里仅用作地名,其地望在殷墟以东,可能是《左传》隐公三年“寻卢之盟”的卢地,在今山东长清西南一带,应当把这个字跟周(琱)字区别开来。
卜辞里的周(琱)地应当是殷的铜矿产地,其地望在殷墟以西。早期(?)组卜辞有伐周(琱)的记载(《合集》20508)。大概在武丁中期殷才牢固控制了周地。因为是铜矿产地,所以卜辞里屡有关于“方”是否会进犯周(琱)和周(琱)地、是否有灾祸的记载(《合集》6728、8454),表明殷人对周(琱)地安危的关注。
还应当提到的是卜辞中有无“周侯”记载的问题。论者每每提到“周侯”,其实是很可疑的。所谓的“周侯”在卜辞中仅一见。这版卜辞原为《甲编》436片。《合集》收为20074片。这版系残辞,行款紊乱,周、侯两字分属两行,并无可能连读。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卜辞中并无“周侯”之称。这个时期的姬周族既以汾相称,其酋长在卜辞中只称为“汾侯”,卜辞无“周侯”之称,应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总括我们前面的讨论,可以得出这样的概述。甲骨文周字为桴(舟)上运载的铜矿石之形,它由桴(舟)得其读音,所以古代文献里周与舟每相通谐。金文周字和小篆周字的递变之迹十分清楚。然而应当注意的是从本义上看它是琱字初文。在卜辞里,周(琱)字和凿连用,指铜矿石——很可能是孔雀石;其余作人名、地名者系指殷王朝直属的铜矿产地及以周(琱)相称的部族,它与姬周方国并无瓜葛。集中出现关于周(琱)的卜辞的武丁时期,姬周族尚居于今晋境,以汾(邠)相称。明乎此,就可以断定殷墟卜辞里的周(琱)与迁今陕地以后才出现的姬周方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了。
三、周族的兴起
周族世系可以武王为界分为两部分。武王灭商建立起周王朝,武王及其以后诸王可称为周先王,而武王以前者则称为周先公。
《国语·周语下》说:“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王始平之。”又说:“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所说“十五王”、“十有五世”之数与《周本纪》合。但此十五世之数曾被人怀疑。《诗经·公刘》孔疏:“虞及夏殷周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许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这个质疑是有道理的。从虞、夏至文王,绝非十五世所能当之。这里面的问题可能出在两个方面:一是“失其代数”(《史记·周本纪》索隐),特别是弃(后稷)以后的若干代,由于时代久远,所以更有漏记的可能。【107】二是误以某一时代的若干世为一世。“后稷”可能即此情况。夏商周的发祥史上屡有世系与时代不能符合的情况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先公世系均为后人追记,时代悬隔,也就难免有漏记和错误。
后稷本为古代农官或农神之称。《国语·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韦注:“柱为后稷,自夏以上祀之。”可见在烈山氏的时代,柱是最著名的种田能手,所以被后人祀为稷神。周的始祖弃曾被尧举为“农师”(《史记·周本纪》),被舜命为后稷,所以有“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说法。周人讲籍礼时说:“及籍,后稷监之。”(《国语·周语上》)可见“后稷”已成为周代农官之名。
在所有古代的稷神和以后以稷为称的农官中,最著名的是周的始祖弃。《诗经·生民》说: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这是关于周族起源情况的宝贵记载。它指明周族的始祖母为姜嫄,《史记·周本纪》则进一步指出她是有邰氏女,有邰氏即居于汾水流域的作为少昊部落一支的台骀氏。诗中的“履帝武敏歆”即践踩帝迹之拇而心动。此“帝”即帝喾高辛氏。姜嫄所以能生下后稷,乃是“克禋克祀”的结果。毛传:“无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郑笺:“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除其无子之疾而得其福也。”郊禖既是禋祀的场所,又是原始部落间男女欢悦幽聚之所在。以后稷为始祖的周族可能是有邰氏和高辛氏于郊禖交往后繁衍出来的一个支族。高辛氏属于黄帝部落,在远古时代,它的播迁相当广泛。相传其首领帝喾曾有四妃,周族始祖后稷、商族始祖契、著名的帝尧以及帝挚均为其子。这个传说表明高辛氏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剔除后人所加入的帝王及世系观念,我们从这个传说里可以多少窥知一些上古部族交往的情况。
后稷所以名“弃”,是因为他曾三次被抛弃: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诗经·生民》)
这种弃子仪式的确切含义,现在难以索解清楚,很可能与原始时代的某种宗教礼仪有关。不管如何,经过严峻考验的“弃”被族人视为神异式的人物则是无疑的。弃不仅出身不凡,而且长大后精于农作: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诗经·生民》)
在古人印象里,后稷的农穑是大有功于民的伟业。《尚书·吕刑》把后稷与伯夷、大禹并列,说“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山海经·大荒西经》也说“稷降以百谷”。农作与天文历法很有关系,所以后稷又是观象授时的能手。《国语·晋语四》:“大火,阏伯之星也,是谓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韦注:“辰为农祥,周先后稷之所经纬,以成善道。”此指后稷观察星辰以掌握农时,所以《国语·周语下》有“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的说法。
需要注意的是,“后稷”可能是周人对其始祖弃的尊称,久而久之,后稷也就成了弃的别名。然而后稷之称并非为弃所独有。《国语·周语上》: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
这里所说的“后稷”就不指“弃”一人,可能自弃以后世为后稷【108】,直到不窋时才失其官。把后稷理解为周族发祥史上的一个时代,要比局限于弃一人,会更近于历史实际。
后稷时代周族所居与禹迹有关。《诗经·閟宫》谓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逸周书·商誓》说后稷“克播百谷,登禹之迹”。禹居之处,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推测,可能在今晋东南和豫西。后稷之居当在今晋东南。
继后稷而起的不窋可能是以能够开挖大的窑洞而著称者。【109】《史记·周本纪》:“后稷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纪》:“后稷纳姞氏,生不窋。”对于这种把后稷与不窋父子排列的说法,学者们多有怀疑。【110】不窋跟后稷一样,可能是周族发祥史上一个时代的名称。《国语·周语上》说他“自窜于戎翟之间”,说明此时周族有所迁徙,可能是从今晋东南北上,至今晋中汾水流域一带。不窋在这里“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脩其绪,脩其训典,朝夕恪勤”(《国语·周语上》),对周族发展做出了贡献,所以周人祭祀时“文、武不先不窋”(《左传》文公二年),以其为重要的先祖代表。
公刘是周族早期的著名先祖。公刘之时周族力量强盛,遂有迁徙之举。《诗经·公刘》对此颇有详细叙述: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关于公刘率族人迁徙的原因,自来有不同说法。毛传认为:“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迫逐公刘。公刘乃避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焉。”郑笺则说:“公刘之去邰,整其师旅,设其兵器,告其士卒曰:为女方开道而行。明己之迁,非为追逐之故,乃欲全民也。”两说相较,郑笺为长。《公刘》指出周人修其疆埸,治理田亩,甚有粮食储积,迁徙别处,“匪居匪康”,原因不是居住得不安康,而是要“思辑用光”,即考虑以此作为团结族人的措施,使周族的优秀传统发扬光大。
公刘率周族所进行的迁徙,可能是沿汾河自北而南行进的。《诗经·公刘》毛传谓公刘迁徙时,“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焉”,可见迁徙规模很大。公刘之迁的最后定居处在今晋西南侯马市以西的稷山、河津、万荣等地。这在《诗经·公刘》里可以寻见某些踪迹。第一,公刘所迁为原上有山之处。“陟则在巘,复降在原”,“瞻彼溥原,乃陟南冈”,毛传:“巘,小山。”郑笺:“广平曰原。……山脊曰冈。”稷山、万荣一带正为原上有山的地形。第二,《诗》谓公刘“逝彼百泉”、“观其流泉”,其居处泉水甚多。《水经注》卷四谓汾阴县南,“平地开源,喷泉上涌”。汾阴为战国魏邑,在汾水之南,今万荣县境。这里的泉水情况与“百泉”、“流泉”之说相合。第三,公刘“豳居允荒”、“于豳斯馆”,其地称豳,确无可疑。《说文》附豳字于邠下。邠称源于汾水,所以公刘之居必在汾水流域。第四,公刘迁居之后,族人“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郑笺:“芮之言内也。水之内曰澳,水之外曰鞫。”诗义表明公刘居住之河相当弯曲。今新绛至河津一段汾河弯弯曲曲,两岸隈隩处当即周人“止旅”地点。
在豳地,公刘率族人“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使大家都有了住处。此后,公刘还做了这样几件大事。首先,举行盛大筵宴,“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诗经·公刘》),目的在于建立组织,维系族众,使周族成为豳地诸旅的中坚力量。其次,通过“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来考察地势,发展农业生产,并“度其隰原,彻田为粮”(《诗经·公刘》),实开周代彻法之先河。最后,公刘建造馆舍时曾“涉渭为乱,取厉取锻”(《诗经·公刘》),到远处采集建筑材料。【111】晋西南地区距渭水不远,周人是步行至渭水,或沿黄河水行【112】而至,已无可考。这件事反映了周族势力在公刘时代已经向关中地区扩展。公刘为周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故《史记·周本纪》讲到公刘居豳时说“周道之兴自此始”。
按照《史记·周本纪》所记周先公世系,公刘之后六传至高圉。高圉及其子亚圉是最早称邠侯者。《今本纪年》载祖乙、盘庚时分别有“命邠侯高圉”、“命邠侯亚圉”的记载。武丁时期的卜辞里有“侯汾”(《合集》9154)、“汾方”(《合集》6659)等记载,此“侯汾”有可能是邠侯亚圉。这些记载表明高圉、亚圉时期的周族势力有了很大发展,并跟商王朝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被列入其外服诸侯之列。周人对高圉、亚圉很尊崇。《国语·鲁语上》说“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将高圉和太王相提并论。春秋时期周王命成简公吊唁卫襄公,其追命之辞说:“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左传》昭公七年)显然,高圉、亚圉在周人心目中具有相当的威望。高圉、亚圉的时代未必如《今本纪年》说的那样具体。若高圉与祖乙同时,那么祖乙至帝辛共18王,而高圉至与帝辛同时的文王则仅6王,显然高圉之后必有失其代数者。大致说来,高圉当在早商后期,亚圉在晚商前期。
在周族发祥史上,公亶父是一位重要人物。《史记·周本纪》称为“古公亶父”,或省称为“古公”。若此,则“古公”当为号。崔东壁曾对此加以辨析,说:“周自公季以前未有号为某公者,微独周,即夏、商他诸侯亦无之,何以大王乃独有号?《书》曰:‘古我先王。’古,犹昔也;故《商颂》曰:‘自古在昔。’‘古我先王’者犹言‘昔我先王’也。‘古公亶父’者,犹言‘昔公亶父’也。”【113】公亶父是使周族兴盛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被周人尊称为“大王”。《鲁颂·閟宫》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序。”迁周族于岐和开始“翦商”事业是公亶父最主要的业绩。
《诗经·绵》对太王迁岐事有较详细的叙述。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其中应注意“率西水浒”一句,因为它指明了太王迁徙的方向和路线。毛传:“率,循也。浒,水厓也。”“率西水浒”即沿着水边往西行进。此水当即渭河。太王率族众从今晋西南处至岐山之阳,正是沿渭河西行。关于太王迁徙路线,《史记·周本纪》还有“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的说法。“漆沮”即《尚书·禹贡》雍州“泾属渭汭,漆沮既从”和渭水“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之所提及者,指“泾水与大河之间流入渭河的洛水”【114】。《水经注》渭水、《史记·殷本纪》正义和《汉书·地理志》颜注均有“洛即漆沮”之说。从今晋西南至岐下,必渡洛水。联系到“率西水浒”之说,可能推测,太王之迁是沿渭河北岸行进的。
周族在太王的时代之所以西迁,原因在于戎狄的威胁。孟子说:“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孟子·梁惠王下》)《史记·匈奴列传》也有“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的说法。此戎狄可能与殷墟第三、四期卜辞里的羌方、危方、召方等有关。
公亶父到岐下后卜居于周原,“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诗经·绵》)。在周原地区,公亶父率族众进行了大规模的建筑: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迺立冢土,戎丑攸行。(《诗经·绵》)
诗中有“缩版以载”的说法,可见当时是用版筑法建造宗庙和家室的。周原包括今陕西岐山县的蒲村、祝家庄、京当、青化、益店以及扶风县的黄堆、法门等乡所属地区。这个地区历年发现了丰富的周文化遗址,还发现有大型宫室以及居住建筑基址,足可与《诗经·绵》等文献记载相印证。
在叙述了公亶父率族众大兴土木的情况以后,《诗经·绵》还写道:“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意思是说周人披荆斩棘之后,道路通畅,混夷奔突窜伏,疲惫喘息而狼狈不堪。这个记载说明在周族迁来以前,周原地区本为混夷居处,太王迁岐之后,周族蒸蒸日上,挤走了混夷的势力。【115】太王在周人心目中有很高威望。周族祭祀“烈祖”时以太王为首(《逸周书·世俘解》),称“三后”(《诗经·下武》)、“三王”(《尚书·金縢》)亦以太王为首。这些应当是对太王率族迁岐功绩的赞颂。
孟子曾认为太王虽然“好色”,但也只是“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而已,“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孟子·梁惠王下》),所以太王并非奢侈贪淫之人。《史记·周本纪》说太王“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则姜女似为太王后妻,很可能是周族和陕境的羌族联合的结果。《左传》僖公五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史记·晋世家》述此事作“大伯亡去,是以不嗣”。所谓“不从”、“亡去”皆不随太王之义,应指不随太王迁岐。过去以为虞仲为西周、春秋时期的虞国之祖,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始为虞国之祖者是太王长子太伯。大约在太王迁岐前夕,太伯率部分族众从邠地南下至今山西平陆一带建立了虞国,事后才被太王承认。所以《穆天子传》卷二有“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之说。至于虞仲则随太王西迁,并于岐山西北的今陕西陇县、千阳、凤翔、宝鸡等地建立了矢国。【116】太王迁岐后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其长子太伯留于邠地,抗拒戎狄,尽量保持周族原有的影响;其次子到岐山西北地区开拓新的势力范围;太王和三子季历居周原,作为周族势力的基地。由此看来,太王时代是周族势力大发展的时代,《史记·周本纪》说周“王瑞自太王兴”,是有道理的。
太王之后,季历继位【117】,称王季。文献关于王季的记载很少。《诗经·皇矣》说:
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
关于王季的业绩,诗中说得很笼统,《史记·周本纪》可能据此而简略地说王季“脩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古本纪年》记载了王季与戎狄斗争的情况: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
文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文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文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西落鬼戎和燕京、余无、始呼、翳徒诸戎的地望,据考证均在今晋境。【118】这表明周族虽然迫于戎狄势力而在太王时西迁,但并未放弃在今晋境的影响。周族势力强大时,今晋境乃是其必争之地,唯其如此,才能进一步完成灭商大业。王季时,商周关系基本上是良好的,这可能是共同对付今晋境戎狄势力的需要。王季曾去朝见武乙,被赐予土地、玉和马匹(《古本纪年》),还曾被文丁任命为殷王朝的“牧师”。《易经·未济》:“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一般认为指周臣名震者以三年时间讨伐鬼方,从而得到大邦殷的赏赐。或以为这和《易经·既济》的“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为同时之事,但不如理解为武乙时王季伐西落鬼戎更为合适。商王朝一方面要联合周族以征伐今晋境的戎狄,另一方面又担心周人势力在今晋境扩展,所以商王朝既赏赐周人,并予王季以“牧师”封号,又“驱汾人”(《合集》31997),以抑制周族势力。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史记·殷本纪》)【119】;其二是“文丁杀季历”(《古本纪年》)。这两件事情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今已无可考。然而却可以认为是商周关系趋于恶化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