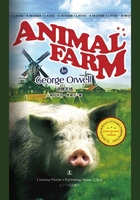偷不难,物还原主——谈何容易!我口袋里揣着带皮套的勃朗宁,前往我的朋友家。
还没进门,便听到从门缝里传出的声音,心不由为之一悸。
“妈妈!还有谁来过?”
隐隐听得老妇人——他母亲的答话:
“水工……”
“出什么事啦?”我边脱大衣边问。我的朋友往四下瞧了瞧,悄悄告诉我:
“今天手枪丢没了……见鬼!……”
“哎——哟!”我说。
老母亲着急地蹲在走道里翻腾篮子。
“妈妈,别干傻事!甭趴在地上了!”
“今天吗?”我问,心里喜滋滋的(他错了,枪是昨天丢失的,不知为什么他以为昨晚还曾见在抽屉里放着),“你们家有谁来过?”
“水工。”我的朋友回答。
“他没进过书房,”他妈妈怯生生地插话,“一进来便去检查水龙头……”
“唉,妈!唉,妈!”
“再没有别人来过?昨天呢?”
“昨天只您来过,除外没有别人。”
我的朋友倏地朝我瞪大眼睛。
“我当然也应列入嫌疑对象。”我语带自尊。
“唉,瞧您那么多心!知识分子就是爱犯这毛病!”我的朋友忙说,“我压根儿没怀疑过您。”
说罢便去查看水工修理过的水管龙头,他妈妈模仿着水道工的动作,甚至模仿着他的声调。
“他进了门,”老妇人说,“说了声‘您好’……把帽子挂到衣帽钩上,便走往……”
“走往哪儿?”
老妇人模拟水道工怎样走进厨房,我的朋友紧随其后,我佯装跟在他俩身后,却抽身拐进书房,将勃朗宁放进——不是左边而是右边的抽屉,然后进了厨房。
“一般情况下,您将它保存在什么地方?”在书房里,我关心地问起。
我的朋友打开左抽屉,朝里面指了指。里面空空如也。
“这就不懂了,”我耸耸肩,“事情真的蹊跷。是的,这像盗劫。”
我的朋友进入了完全绝望的境地。
“不过,我还是以为不会被偷,”我停了停,又说,“试想:既然没人来过,怎能被盗呢?”
我的朋友随着我的话跳将起来,去前室掏旧军大衣的口袋。什么也没找到。
“这样看来是被窃,”我沉思着说,“应去民警局报案。”
我的朋友又是唉声,又是叹气。
“您不会塞到其他什么地方吧?”
“我从来都放固定地方!”我的朋友焦急地说。为了证明所说属实,他打开中间的抽屉,后来又喃喃着打开左抽屉,甚至伸手摸了一遍,而后拉开下面的。最后他一边诅咒,一边打开右抽屉。
“原来在这里!”他嘶哑着嗓门对我说,“哈,妈,找到了!”
这天他特别高兴,因此留我吃了午饭。
一直悬在心上的手枪问题解决以后,我迈出了可说是危险的一步——辞去了《河运报》社的职务。
我转入了另一天地,常去鲁道菲那里做客,结识了很多作家,其中一些还很有名望,只是如今都已忘记。只一件事没忘:经鲁道菲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出版商马卡尔·勒瓦茨基。
鲁道菲一切皆备:才智,敏悟,甚至博古通今,就缺一样——钱。但他偏偏热爱自己的事业,无论天大困难,也要出他的厚杂志。如果要他放弃,我以为他非死不可。
为这原因,我忽然置身于一个奇怪处所,或如鲁道菲所说,出版商勒瓦茨基的办公地。它位于莫斯科某条林荫大道上。走到时我首先大吃一惊,门上挂的招牌是:照相器材供应处。
更使人吃惊的是里面根本没有照相器材,只有几卷报纸包的印花布和呢料。
但里面依然人头济济。来的人均身穿大衣,头戴礼帽,热切地交谈,从我耳边刮过“钢丝”、“罐头”等字眼。我感到惊奇,别人也在惊奇地瞪我。我道明来意,说是来找勒瓦茨基先生办事的,他们客客气气地把我领进板壁后面。到了里面,我的惊讶上升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勒瓦茨基身前的办公桌上堆着两包鲱鱼,一包比一包大。
但使我不喜欢勒瓦茨基并非因为办公桌上的鲱鱼。勒瓦茨基本人是个小个儿,瘦得像干瘪枣,身上穿的不像我眼熟的《河运报》人那种普通短打,而是很出奇:长礼服、条纹裤、脏浆领,浆领上系一条绿领带,绿领带上别一枚红宝石领夹。
勒瓦茨基使我不悦,而我使得勒瓦茨基害怕,更确切地说,使他感到沮丧,因为我向他陈述了来意:为在他的杂志上发表我的小说签订合同来的。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常态,接过我带来的一式两份合同,掏出自来水笔,几乎看都不看便签了字,旋即将合同连带自来水笔推到我鼻子底下。我拿起笔,睨眼瞧了瞧两个纸箱,纸箱上贴着“阿斯特拉罕上等鲱鱼”的标签,还画有一领渔网,渔网旁坐着个卷起裤筒的渔夫,我忽然犯了疑。
“是不是签过合同就付款?”我问。
勒瓦茨基的脸从上到下顷刻间化成一个甜蜜的、殷切的笑。
他干咳一声,说道:
“两星期后如期付款,眼下手头紧……”
我放下笔。
“或是一星期以后,”勒瓦茨基赶忙道。“您为什么不签?”“不妨等您手头不紧时再签。”我说。
勒瓦茨基苦笑着摇摇头问:
“您不相信我?”
“哪能呢!”
“星期三!”勒瓦茨基慷慨许诺,“如果您真缺钱花。”
“请原谅,不能啊。”
“主要的是签好合同,”勒瓦茨基分析给我听,“钱嘛,也可以星期二提前兑现。”
“请原谅,不能。”我推开合同,扣上上衣衣扣。
“等等。唉,瞧您这人!”勒瓦茨基叹了口气,“人们还说作家是不讲实际的人哩。”
他露出了悒悒之色,不安地朝四下张望。就在这时进来一个年轻小伙,交给他一张用白纸裹着的马粪纸车票。“那是张卧铺票,”我想,“大概他要去什么地方……”
出版商顿时红光满面,眼睛亮亮的——我万万没有料到。
长话短说,勒瓦茨基当场付给了我合同上写的那笔稿酬,一部分是现款,一部分是期票。我持有期票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此颇为得意(为这张期票我后来好一阵子奔忙,为了兑现,我曾坐过发散着浓烈皮革味的箱子干等,此乃后话)。
稀里糊涂过了两个月,其间曾找鲁道菲发过牢骚,说不该叫我去找勒瓦茨基这样的出版商:长那么一双浑浊的眼睛,别那么个花里胡哨的宝石领带夹,开那么一张期票。鲁道菲回答:“把那期票让我瞧瞧。”看罢不在意地说:“一切正常。”
我第一次拿期票去取款时的情景永志不忘。“照相器材供应处”忽然换成了“医疗器皿供应处”的招牌。
我走进去对他们说:
“我希望见马卡尔·鲍里索维奇·勒瓦茨基。”
我清楚记得,当听到回答说马·鲍·勒瓦茨基已经出国时我怎样两腿发软,我那颗心……
啊,我那颗心差点儿……不过,现在说来已不重要。
简单地说,在胶合板墙后坐着的是勒瓦茨基的胞弟阿基洛伊济。此人与他胞兄有天渊之别:田径运动员的强健肌肉,沉甸甸的一双眼睛。他付了到期该付的那笔钱。
又过一个月,到了第二次贴花兑现的日子。我苦了我一双来回奔命的腿,方得以在一个官方机构里拿到现钱(拒付期票,后来送到了一个有铁栏铁窗的公证所或者银行)。
第三次我学乖了,到期两星期前便去找勒瓦茨基的胞弟,说我那双腿已经吃不消。
勒瓦茨基第一次用正眼看我:
“我理解,何必一定到期,现在就可换成现钱。”
我拿到了不是八百而是四百卢布。即使如此,我还是怀着极其轻松的心情,把两张方方正正的贴花交给了勒瓦茨基的胞弟。
啊,鲁道菲,鲁道菲,多谢您,也多谢勒瓦茨基的胞弟阿基洛伊济!
我给自己买了件大衣。
那一天终于来到了。我冒着严寒重访挂有神奇招牌的那幢楼房。时间是夜晚。一百瓦的灯光刺得眼睛发痛。灯下既没有了勒瓦茨基哥哥,也没有了勒瓦茨基弟弟(还用说!弟弟也远走高飞了),只坐着个连大衣都没脱的鲁道菲。桌上桌下以及地板上堆满了刚印就的瓦蓝封面的《祖国》杂志。啊,这瞬间!——现在想来未免滑稽可笑,但那时我少不更事,激情太多。
鲁道菲的眼睛熠熠发亮。应该说,他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算得上是位有勇有谋的好编辑。
当然你们在莫斯科常常见过有那么一些年轻人,他们不是作家,但每当新一期杂志刚刚印就,便麇集在编辑部;他们不是演员,但每当彩排总是在场;他们虽不作画,但逢美术展览无一缺席;对歌剧中的女主角亲切地呼她的名字和父名,对领导者也一样,虽与之并不认识;在大剧院,首场演出时他们总是坐第七、第八排,向楼座上的熟人挥手致意;在大都会饭店,他们坐的桌子总是临近喷水池,让彩灯照在他们的喇叭裤上。
鲁道菲面前就坐着那样的一个人。
“请说说您对我们新一期杂志的看法。”鲁道菲向年轻人讨教。
“伊利亚·伊万诺维奇!”年轻人拨弄着手里的书兴奋地说,“文章篇篇出色。但是,伊利亚·伊万诺维奇,请允许我冒昧直言,我们,您的读者,不明白为什么选登马克苏多夫写的东西,它只能糟蹋您的杂志。”
“不得了,这一期杂志连带遭难!”我周身发冷。
但鲁道菲偷偷向我眨下眼,问:
“能否讨教?”
“既然如此,”年轻人当即应道,“您是允许直言不讳的了,伊利亚·伊万诺维奇?”
“请说无妨。”鲁道菲容光满面。
“第一,文理不通……我可以指出二十处犯有严重语法错误。”
“应该检查一遍。”我提心吊胆地想。
“而那语体!”年轻人继续说道,“天啊,多么吓人的语体!除开这点不谈,它纯属生搬硬套,加点儿廉价的哲学,肤浅的说理……平淡,无味,伊利亚·伊万诺维奇!此外他是模仿……”
“谁?”鲁道菲问。
“阿韦尔琴科[1]!”年轻人掰开书页,侃侃而谈,“最最平庸的阿韦尔琴科!我现在就指给您看。”年轻人开始翻寻,而我像鹅那样伸长脖子注意他的手指。可惜,他未能找到。
“我回家后找它出来。”我想。
“我回家后找它出来,”年轻人许诺,“老实说,写得不好,伊利亚·伊万诺维奇。他只是粗通文墨!他是什么人?什么文化程度?”
“他说是教区小学毕业,”鲁道菲回答,眼睛睁得亮亮的,“不过您可以亲自问他本人。请你们两位认识一下。”
年轻人脸上倏地生起一团晦气,眼中充满难以言喻的恐慌。
我向年轻人一鞠躬。他哎哟一声,痛苦使他龇牙咧嘴,脸蛋变了形,赶快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子。这时我方看到他脸颊上流的血,不由愣住了。
“您怎么的啦?”鲁道菲高声问。
“钉子。”年轻人只回答了半句话。
“告辞诸位。”我低声向两人道别,不过尽可能将目光避开年轻人。
“请您把书带走。”
我接过赠书,握别鲁道菲后向年轻人鞠了一躬。对方用手帕捂住脸颊(以致手中书和手杖统统落到地上),连连后退,却又一不小心胳膊肘碰了桌子。但他管不了许多,抢先走了出去。
飘着大片大片的雪花,漫天飞白。
值得描写我如何通宵达旦地把年轻人指摘之处一读再读吗?!初时倒还觉得所写瑕不掩瑜,但过不多久便发觉一无是处,天明时我已惭愧得浑身哆嗦了。
第二天发生的事记忆犹新。早晨我那失而复得手枪的朋友来访,我赠了他一册小说。晚间我参加作家们的一次聚会。聚会是为了庆祝重大事件——名作家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国外归来。庆祝气氛又因另一作家叶戈尔·阿加佩诺夫出访中国返抵而益发热烈。
我整衣赴会,心中激荡不已。不管怎么说,它是我为之向往的新天地,这新天地即将展现在我面前,而且展现的是它最好的方面——出席晚会者应是文艺界一流人物,代表着绚丽多姿的文坛。
果然,一进屋,便感到氛围之愉悦。
首先看到的是昨晚被钉子划破脸的年轻人,虽则整个脸庞包扎在新纱布里,我还是认出了他。
他见我如见亲人,显得非常高兴,久久拉住我的手,一整夜都在重读我那小说,重读之后使他由厌恶变为喜欢。
“我也一整夜重读了自己的小说,”我告诉他,“重读之后使我由喜欢转变为厌恶。”
亲切交谈时他顺便透露给我一个新消息:上席的菜肴中将包括冰镇鲟鱼。总而言之他很高兴、激动。
我朝这放我入内的新天地打量了一下,也由衷地感到高兴。餐厅宽敞,席上摆有二十五份左右餐具,酒杯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连黑鱼子也被照得亮闪闪的,葱绿的腌黄瓜使人想起豪放而欢快的野餐。经介绍我认识了大有名望的作家列索谢科夫和通斯基。太太们不多,但也有几位。
利科斯帕斯托夫不声不响地躲在客人中间,可能他比来宾低一台阶,甚至比不上栗色鬈发的列索谢科夫,当然,更不用说阿加佩诺夫或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样的名流。
他挤过人群向我走来。我们相互问好。
“得,”不知为什么他叹了口气,“祝贺你,衷心祝贺你。我对你说白了吧,你人挺机灵,老弟。那时候,即使砍断我手,也不信你的小说能够发表。你用什么法儿打动了鲁道菲的心?看你外表挺文静……但文静之中……”
这时正门门铃大响,打断了利科斯帕斯托夫的说话。执行主人职务的文学评论家孔金(晚会就在他家举行)大声宣布:“他来了!”
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莅临。前室里响起了清脆的嗓音和接吻声,接着步进一位小个子公民,身穿赛璐珞领短上衣,脸带怯生生的、恭敬的表情,手里拿顶帽子。那上面围着个天鹅绒帽箍,还留着蝴蝶结的印记。不知为什么他不把它留在前室。
“莫非出了差错?”我暗想。来人外貌无论如何跟从前室里传来的爽朗笑声和对“露馅大馅饼”的赞词对不上号。
确实如此。小个儿之后,又有一位高大魁伟的美男子,带着他那飘飘散散、保养得很好的胡子和一头梳理得体的鬈发,由孔金搂住腰引进餐厅。
来宾中有小说家菲阿尔科夫(鲁道菲跟我咬耳说此人平步青云,踌躇满志),穿戴算得考究了,但与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衣服相比,未免相形见绌。由巴黎一流裁剪师用一流面料缝制的咖啡色西服,穿在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匀称、丰腴的身上简直美不胜收,更何况内衣是浆过的,皮鞋是光漆的,衣扣子是紫晶的。他朝丰盛的酒席扫了一眼,张嘴露出白亮亮的牙齿,高声赞道:
“哈,不赖!”
立时扬起一片笑声、掌声、接吻的声音。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与一些人握手问好,与另一些人接吻,对一些人开玩笑地故意扭头去,还用白净的手掌挡住脸,像怕见光一般,而且打了一个响鼻。
他大概把我错认作另一人,连连吻了三次,把他的白兰地酒味、香水味和雪茄味儿一股脑儿送进我的鼻子。
“谨向诸位介绍,”他指着首先进来的小个儿介绍,“巴克兰扎诺夫,我的朋友。”
巴克兰扎诺夫一笑,但像个殉难者,大概因为身处陌生的社交场合感到羞涩,错把他手里的帽子戴到了手执电灯的一尊巧克力色少女雕像上。
“是我把他拉来的,”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道,“反正他在家中无事可做。我仅向诸位介绍,他是个极好的人,博学多才,不用一年,他将要胜过我们大家,请记住我这话!巴克兰扎诺夫,见鬼,干吗把帽子挂到雕像上?”
巴克兰扎诺夫正要与人寒暄,但事违心愿,因为来宾忙着入席,开始上香喷喷的大馅饼了。
宴会的气氛欢快、热烈、友好。
“哈,露馅大馅饼!”传来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声音,“巴克兰扎诺夫,你知道咱们为什么吃大馅饼吗?”
碰杯声叮当悦耳,似乎枝形吊灯又添光辉。三巡过后,大家的目光集中到了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身上。“谈谈巴黎!谈谈巴黎!”众人央求道。
“行,举个例。一天,我们去参加汽车展览会。举行了揭幕式,如此这般,新闻记者,发表演说……在记者中间,站着我们的痞子萨什卡·孔秋科夫……当然,由法国佬出台讲话,致简短贺词……自然,开了香槟。我一瞧,孔秋科夫的腮帮子鼓鼓的,我还没来得及眨眼,他就呕将起来。太太、小姐、部长都在场呀!可他这狗崽子……头脑里不知犯了什么病——至今未弄明白——把宿酒吐了他旁边的人一身,这就吵翻了天。当然,部长装作没事样儿。但,怎能没事呢?燕尾服、礼帽、裤子值得三千法郎!后来喂他水喝,领了出去……”
“再说一个!再说一个!”众人一致嚷嚷。
腰系白围兜的女佣开始上鲟鱼,碰杯声益发响亮,有人已改用大嗓门说话。但我一心一意想了解巴黎。在喧哗声中仍竖起耳朵听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巴克兰扎诺夫!为什么不动你的叉子?……”
“往下说,我们恳求您。”那年轻人首先鼓掌……
“再说一个!”
“在香榭丽舍大街两个恶棍相逢,分外眼红……这边还没来得及回头,那边便张嘴啐这边的猪脸……”
“哎哟哟!”
“是呀……巴克兰扎诺夫!你这家伙别尽打瞌睡!……不料那个神经衰弱的伙计没啐准,啐到了一位陌生太太的帽子上……”
“在香榭丽舍大街?”
“你想想,这是体面人溜达的场所!那太太的帽子价值三千法郎!旁边的先生当然不客气,照他头上一棍子……吵翻了天!”
有人操手鼓掌,杯光交错,我们都为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健康举杯。
他又讲起了巴黎逸事:
“他脸都不红一红地问对方:‘多少钱?’而对方,那个拉皮条的(他说时甚至眯起眼睛)说:‘八千!’这边道:‘给!’伸手做了个下流姿势。”
“就在大歌剧院?!”
“你想想,他哪管这是大歌剧院?!那时第二排还坐有两位部长。”
“对方呢?对方怎样回敬的呢?”有人笑嘻嘻地问。
“破口骂娘。”
“天哪!”
“当然,两人都被带走。在那儿,处理这样的事很简单……”
欢声笑语更浓,酒入微醺之时,我觉得脚底下软乎乎、滑溜溜,低头一瞧:一块鲑鱼肉。谁掉下的——无从知道。反正欢笑声淹没了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说话,使我不能再饱耳福。
我还未及好好消化他讲述的外邦奇闻,门铃报出叶戈尔·阿加佩诺夫莅临,又少不了一番混乱。隔壁房里有人在钢琴上弹奏狐步,我的年轻朋友已拥着一位太太翩翩起舞。
叶戈尔·阿加佩诺夫兴高采烈地、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后面是个矮小、干瘪、黄脸、戴黑框镜的中国人,中国人之后是位身穿鹅黄裙衫的太太和一个名叫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的大胡子。
“伊斯梅伊尔在这里?”叶戈尔问,旋即向他走去。
对方哈哈笑道:
“哈,叶戈尔!”便把胡子埋进阿加佩诺夫的肩窝里。中国人朝所有的人一味亲切地笑,但不发声,后来也没吐过一字。
“请诸位跟我的中国朋友认识一下!”叶戈尔推开伊斯梅伊尔,大声说道。
但欢声迭起,大家乱作一团,谁还理会得!人们在房间的地毯上也跳起舞来,使得房间越发拥挤。书桌上乱放着咖啡杯。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在啜白兰地。巴克兰扎诺夫在椅子里睡熟了。房里烟雾弥漫。我觉得已是到了回家的时候。
但出人意料,阿加佩诺夫突然找我交谈。那是后半夜的三点钟,他脸上带着惶惶不安的表情,找这找那说话,并且据我所知,遭到拒绝之后来找我的。此时我正埋在靠书桌的椅子里喝咖啡,俯首思忖为什么心里不是滋味,为什么倏地觉得巴黎生活太无聊,我不再有亲履其境的念头。
忽地向我俯下一张戴大眼镜的阔脸。这就是阿加佩诺夫。
“马克苏多夫?”他问。
“敝人便是。”
“听说过,听说过,”阿加佩诺夫连道,“鲁道菲曾向我提起,说您发表了一篇小说?”
“是。”
“说是篇锋芒毕露的小说。啊,马克苏多夫!”他蓦地朝我眨眨眼,悄声道,“请注意那位人物……见了吗?”
“那大胡子?”
“是他,我的内弟。”
“是作家?”我问,同时端详着瓦西里·彼得罗维奇。
“不,是从捷秋莎来的合作社社员……马克苏多夫,不要失去机会,”阿加佩诺夫劝说我,“切莫失之交臂。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很少有,在您创作生涯中不可多得。用他的广见博闻一夜可写成几十个短篇,每个短篇保证走俏。古代文物,鱼龙花草,青铜世纪件件皆通,他讲起历史来准叫您目瞪口呆!抓住他吧,否则别人就将抢过手去,借他拉屎撒尿了。”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感觉得出在谈他,所以微微露出笑容,但那是惴惴不安的笑。他喝干了杯中的白兰地。
“最好的办法……有了!”阿加佩诺夫说,“现在就介绍你俩认识……您是单身吗?”
“单身……”我瞪大眼瞧着阿加佩诺夫说。
阿加佩诺夫一团高兴:
“太好了!你俩认识一下,然后带您府上过宿!好办法!您总有沙发吧?他在沙发上也能将就,不添麻烦,住上两天就回去了。”
除震惊外我无以答复,只说了一句:
“我只一张沙发……”
“宽大不宽大?”阿加佩诺夫语带不安。
幸好我醒悟过来,且很及时,因为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已开始扭动身子,显然准备与我认识,而阿加佩诺夫已开始拉我的手了。
“请原谅,”我说,“可惜留不得。我是与人合住的套间,后房里睡有女房东的几个孩子(我打算补上一句,说孩子们正患猩红热,后来一想,谎话过分出格,但到底还是说出了)……他们正患猩红热。”
“瓦西里!”阿加佩诺夫高声叫唤,“你患过猩红热吗?”
在我一生中,无数次听到人们骂我是“知识分子”。我不想争辩,也许我活该冠以这么个伤心的头衔。但这次终于鼓起全部勇气,乘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带着哀伤的笑容只说了“曾……”时,我毅然决然告诉阿加佩诺夫:
“我坚决拒绝他来过宿。不能。”
“可否将就着点儿?啊?”阿加佩诺夫悄声问。
“不能。”
他垂下头,嚅动着嘴唇。
“原谅我说一句:他是来看望您的,不住您府上又住哪儿呢!”
“所以他才在我家住了下来,见鬼。”阿加佩诺夫怅然道。
“既然……”
“可今儿来了我岳母和她妹子,您明白吗,亲爱的朋友?身边又有这中国朋友……妈的!这些外亲内眷都赶热闹来了。安安静静地在捷秋莎岂不更好!……”
阿加佩诺夫说罢掉头而去。
我不知怎的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恓惶之感,所以除孔金外不与任何人打招呼,便走出了这幢楼房。
注释:
[1] 阿韦尔琴科(Apkaauǔ TumopeeBuy ABepyehko,1881—1925),实有其人,系俄国作家,他的剧本和讽刺小品嘲讽了庸俗的资产阶级生活,著有《欢乐的牡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