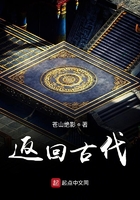梁永生又安了新家。
这是一所破旧的闲院子,坐落在宁安寨的尽东头。它的前边,是一片杨树林子。东边是平展展的田野。西边是尤大哥的住宅。在这宁安寨拐了个弓弯的运河,从这所院落的后面悄悄流过。院内房虽不多,好在永生没啥东西,只不过是几口子人,挤巴挤巴倒满能住下。
这个住处,是梁永生托尤大哥给他找的。
在永生要另起炉灶自己安家的时候,魏基珂老两口子说啥也不干。可永生长短不听,死说活说不变卦。魏大叔和魏大婶万般无奈,只好把这条耿直汉子和他的家眷送入新居。魏大叔、尤大哥还有附近的一些穷爷们儿,这个拿来一些吃的,那个送来一些烧的,还有的匀给他一些随手使用的家什,这么七拼八凑,齐打忽地一操扯,总算帮助永生一家安起了锅灶。
梁永生为啥高低要从魏大叔家搬出来呢?一来是,梁永生觉着魏大叔的穷日子皮儿包着骨头,三天两头闹饥荒,架不住他这一家子糟扰;二来,也是主要的,是从疤瘌四上门逼债引起的——
这天下午,魏大叔两口子和孩子们都出去了,家里只剩下了永生和翠花,突然疤瘌四鬼鬼祟祟地闯进宅来。疤瘌四仗凭两片子嘴唇会网花,在白眼狼手里闹得挺红火。今天他奉命来打探,又是一个立功得宠的机会,心里当然高兴,所以他一进门就皮笑肉不笑地嚷道:
“梁永生可在这里住吗?”
正在给鸡拌食的杨翠花,搭眼一瞅,不认识。可是,她从这个家伙的衣着、神色满可看出——不是个好蘑菇!于是,她紧走几步,站在屋门前,挡住疤瘌四问道:
“你是干啥的?”
“哦!不认识?我是龙潭街上贾永贵——贾二爷的账房先生……”
疤瘌四一提到“贾二爷”,脸上是那样的卑贱。可是,翠花一听,心里的气就满了。她又问:
“你要干啥?”
“我找梁永生——”
“他不在!”
“哪去啦?”
“出去啦!”
“噢!你大概就是他那孩子的娘吧?”
“你也甭问是爹是娘,有话就说吧!”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法?”
“天生的就是这么说话,凑合着听吧!”
疤瘌四这个老滑头,是把白铁刀,样子挺神气,一碰硬就卷刃。现在他当然能看出,杨翠花是故意跟他怄气。可他觉着在这里耍威风怕是没光沾,只好佯装不察地又说:
“你别误会,我和梁永生是老相识,听说他回来了,来看望看望他,还想帮帮他的忙……”
“帮他啥忙?”
“给他找个饭碗。”
“啥饭碗?”
“贾二爷家还少个长工……”
“你回去告诉他吧——”
“妥啦?”
“不去!”
“贾二爷已经向我言明:工钱加倍……”
“他有工钱,俺有志气——侍候不着他!”
疤瘌四见杨翠花净戗着他来,把那疤瘌眼儿一斜立:“你可别忘了——二十多年前,你们还欠东家一笔账呢!”
“我们和白眼狼那笔账,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好!当初是四升棒子,如今过了二十多年……”
“变成多少啦?”
“一百三十四石五斗六升!”
“好吧!”
“还得起?”
“有数就还得起!”
“那更好了!可空口白话不中用,就请你拿出粮食来清账吧?”
“俺跟你清不着!回去和你主子学学舌——我们早晚是要跟他清账的!”
疤瘌四像条当头挨了一闷棍的哈巴狗,找了个没味儿,夹着尾巴溜走了。
这一切,梁永生在屋里听了个清清楚楚。不知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出面。当翠花回到屋时,他高兴地说:
“好!你不是鼻子不是脸地给他那一套,满好!”
翠花问:
“你琢磨着,他这是来干啥呢?”
永生说:“你们方才在院里说着,我就想好啦——什么‘请长工’呀,‘逼旧债’呀,全是闲扯淡!很可能是白眼狼派他来探风儿的!”
“探风干啥哩?”
“又要在咱身上打什么坏主意呗!”永生说,“看来要出事儿了——咱得想个法儿,要万一碰上什么磕绊,好别连累上魏大叔……”
第二天,他们就搬到这个闲院子里来了。
几天来,永生借了副锢漏挑儿,天天外出盘乡。
他盘乡的目的,除了挣几个钱糊口而外,还有一个比这更占主要的想法,就是要借盘乡之便,到周围各地,去扫问扫问共产党和红军的消息。
今天,他又特地远出,到城根底下盘了一趟乡。原来他以为那一带消息灵通,兴许能扫问着共产党和红军的信儿,可是,还是没有打听到什么准信儿。
阴沉的天气渐近黄昏。
风沙吹打着新糊的窗纸。
梁永生风尘仆仆地回到家,把锢漏挑儿一撂,侧到被窝卷儿上,正架起腿来抽闷烟,二愣姥爷嚓嚓走进屋来。这一带的风俗:越不系外,越不打招呼;这更显得亲近。二愣姥爷坐在炕沿上,把那皱皱巴巴的手伸进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永生说:
“我那个小子打来一封信。你给我看看,上头写了些啥意思。”
永生直起身,接过信,又划着火柴点上灯,从信皮儿里把信瓤儿抽出来,凑在灯前默默地看开了。
闪闪烁烁的灯光,只有黄豆粒那么大,突突地冒着烟子。可能是因为灯草快够不着油了,这已经很微弱的光亮还在逐渐缩小。不知是因为灯光太弱,还是因为信中写了些什么叫人不高兴的事儿,只见梁永生越看脸色越沉,两眼越瞪越大,眉间也聚起个疙瘩。
二愣姥爷不去理睬永生的表情。他在永生看信的当儿,耷拉着脑袋装上一锅子烟,然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在火石上,乒噌噌乓嚓嚓地打起火来。
一只在院中俯冲低飞的燕子,瞅了个人们不注意的空隙钻进屋来,打了一个圈儿又飞走了。
二愣姥爷一边打火,一边像在跟火石说话似的,断而又续、续而又断地自己叨念:
“几个月前,他来过一封信……那封信上,写的是他们工人们闹斗争的事儿……那信上说的,可叫人高兴啦——工人们提出几个条件,大老板不想承认,又不敢不承认……打那以后,我这个老头子的心里,也像点起了一把火,成天价盼着……”
二愣姥爷嘟嘟囔囔说到这里,撩起眼皮看了永生一眼,只见永生早就把信看完了,信瓤已经撂在桌子上。这时的梁永生,仰在被卷上,两手交叉托着后脑勺,瞪着两只大眼瞅屋梁,仿佛正在想着什么。二愣姥爷赶紧撂下他那没说完的半截话儿,向前就一就身子,凑在永生脸前,盯着他那忧思重重的神色,问道:
“信上密密麻麻那一大片,净写了些啥?是他们工人跟大老板闹斗争的事儿不?”
“是!”
“如今闹胜了不?”
“蒋介石那个孬种,镇压工人运动……”
永生气冲冲地先说了这么一句,把思路从沉思中收回来,将信上的内容从头到尾跟二愣姥爷说了一遍。
二愣姥爷的耳朵有点背了。他侧歪着膀子,并用手掌帮助耳轮,捕捉着从永生嘴里发出的每一个字音。听完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用一种气愤、惋惜和自慰相混合的语气说:
“实指望工人们成了气候,咱这庄稼人也跟着沾点光呢,不承望又叫蒋介石那个混世魔王给搅了!唉,算啦!稀里糊涂、凑凑合合地过吧……”
永生劝了他几句。他又说:“像我这个,老老搭搭的了,还能活几天呀?我是愁着你们这些年轻人没法熬哇!”
二愣姥爷说了些泄气话,抬起屁股走了。
他这些话,在梁永生的心里,掀起了层层波涛,激荡着心弦,撞击着胸壁。原来永生过去听人说过工人运动的事,并且他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工人和农人,都是受穷受苦的人。一旦工人们闹出个名堂来,乡间的穷人们也许就有个奔头了……”现在他看了这封信,心里很苦闷。不由得暗自想道:“就真的像二愣姥爷说的那样,稀里糊涂地过下去吗?不!不能那样窝窝囊囊地活一辈子!可又怎么办呢?”
永生正然沉思,屋外传来一阵咕咚咕咚的脚步声。
接着,哐当一声,屋门开了。一股凉风吹进屋,扑灭了桌上的油灯。梁永生随手点上灯,只见一位生着连鬓胡子的红脸大汉,像个半截黑塔似的站在眼前。他那胖乎乎的脸上,好像暴雨欲来的天空,阴森森的;一张一合的大鼻孔里,喷着火焰般的热气;两颗网满血丝的大眼珠子,闪射着愤怒的光芒;他那虎彪彪的身躯,仿佛也在微微颤抖。梁永生木愣愣地望着眼前这位熟人,好像感到十分生疏;由于纳闷儿,他脸上的神情也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他初而喜,继而惊,尔后惊喜交加地开了腔:
“大虎哥!你从哪里来?”
“龙潭!”
杨大虎顺口扔出两个字,抽下掖在腰带上的毛巾擦着汗,坐在板凳上。接着,他又一面掏出烟袋装着烟,一面呼哧呼哧喘大气,还是不吱声。我们的语言,的确是有没有能力来表达感情的时候。看大虎这时的表情,分明是装着满满的一肚子话,恨不能一下子全向永生倾诉出来,就像喉头被一种什么东西堵住了,使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仿佛那些一齐向外攻的话,由于挤在一块儿谁也攻不出来,憋在胸膛里,撑得胸脯子忽闪忽闪直鼓涌。
梁永生望着大虎的表情,心里火辣辣的,暗自纳起闷儿来。杨大虎留给永生的印象,是个大大咧咧的脾气,乐乐呵呵的笑面。当永生在天津街头遇见大虎时,大虎一下子抱住他,亲热得恨不能啃两口。从那以后,又是四五年没见面了,这回一见面儿,怎么竟是这样一种神色呢?说真的,在大虎没来之前,永生早就想和大虎哥见个面儿。并且,他还曾情不自禁地预想到乍见面的情景——鲁鲁莽莽的杨大虎,一定会亲亲热热地抓住他,兴许还会给他一撇子,然后说长道短,问这问那。可他今天的表情,怎么简直判若两人?这到底是咋的回事呢?永生一面悄悄地想着,一面用两条目光往大虎的心里钻探。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眼时下,理智对大虎已经失去了控制能力,大虎现在的行动,几乎完全是被一种冲动的感情驱使着。正在这时,外边不知是谁家的孩子放了几声鞭炮。这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使永生蓦然想起,后天又是元宵节了。于是,永生为了把大虎的思路从冲动的感情中引开,就说:
“大虎哥,后天又是元宵节了,今年你还引狮子不?”
“引狮子?我要打狼了!”
“打狼?”
“对!”
这时,大虎的心情也平静些了。他一面抽着烟,告诉永生这样一件事情——
前天,大虎因不愿再给白眼狼拉套,想辞活不干了。白眼狼一听可毛了脚。一个长工,辞活不干,这有啥值得毛脚的呢?因为白眼狼相中了大虎这身好力气。拿耪地来说,他的锄杠比别人的长着一尺,别人一天耪二亩还得起早贪黑,大虎一天三亩地两头见太阳。说到担水,他不干则罢,要干,都是两条扁担同时上肩。有一回老牛惊了车,好几个人拽不住,他腾腾赶上去,抓住缰绳一蹲身子,车就刹住了。从那,人们给起了个外号,叫“气死牛”。杨大虎这身好力气,在白眼狼的眼里,是很有分量的。因为白眼狼的看法是:沙里能澄金,水里能捞鱼,穷鬼的血汗中能捞出无穷富贵。因此,白眼狼对每一个长工,只要汗没流干,油没挤净,他是想尽法儿也不叫人家离去的。你想啊,像杨大虎这个大有潜力可挖的长工,他怎肯松手呢?
于是,他装出笑脸说好话,张着狼嘴许大天:
“老杨啊,你、你好好干吧,我、我准亏不了你……”
大虎腻味他这套虚情假意,就把脖子一横,不费思索地、干掰截脆地说:
“说这些没盐没酱的淡话做啥?结账吧!”
“你、你为啥不干哩?总、总要说个理儿呀!”
“俺卖的是力气,挣的是工钱,人并没卖给你!”
白眼狼脸上那一丝儿强挤出来的笑容,像被一阵硬风吹灭了的灯亮一样,刷地消失了。接着,他收起软的又端出了硬的:
“长、长工长工,就、就得长干;我、我这里不是开店,不、不能那么随便!”
大虎虽没有梁永生那叱咤风云的气魄,可他也不是逆来顺受的认命派。这时他一听火了,忽地站起来,指着白眼狼质问道:
“你说啥?咱找个地方说理去——”
白眼狼为了把大虎这股虎劲儿唬回去,冷笑道:
“你、你要跟我打官司?那、那我花上几个钱,就轻而易举,买、买你这条命,叫、叫你做第二个梁宝成!”
……
梁永生一听白眼狼这么狂气,心里很生气,不知不觉地把捏在手里的一根火柴棍儿捻碎了。他问大虎:
“你怎么回答的?”
杨大虎气冲冲地说:
“我一把抓住了那个老杂种的脖领子,吼道:‘现在就走!就算刀抹脖子,我也得吐出这口气来!’”
“对!就是这样答对他!”永生说,“他怎么样?”
“他吓瘫了!紧说好的——什么‘伙东一场是有缘啦’,‘一个锅里抡马勺这么多年啦’,净是些草鸡毛话儿!”
“叫我看,他并不怕你上县政府,他知道你也不真去跟他上县政府。”永生说,“他大概是怕你把他弄出去掏出他的五脏。”
“我就是打算那么办!”
“以后怎么样啦?”
“以后马铁德那个孬种闯进来了,他一看不妙,又打圆盘,又赔不是,并许给我:账房先生外出回来,马上结账,该多少是多少,分文不会少——”大虎说着说着又上了气。他一拍桌子说:“谁知他妈的这是用的一计!”
“啥计?”
“两天以后,就是今天,他派了几个狗腿子,把我的儿子给抓去了!”
“长岭?”
“对!”
“他不是出门了吗?”
“在外头跑了几年,混不下去,又回来了。”
“抓他干啥?”
“说他是共产党!”
“他真是共产党?”
“要真是又好啦!就连他们也知道长岭不是共产党。”大虎说,“我听说,他们是这么谋划的:把长岭抓了去,来个屈打成招,然后押送县府……你想啊,长岭进去还有个出来?连我这条老命怕是也得一勺子烩进去!……”
杨大虎说到这里,梁永生的肺都要气炸了。激怒使他的面颊红晕起来。他觉着像有块咸腥的东西,堵住了他的喉头,一时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子,他问大虎道:
“大虎哥,你要怎么办?”
“依着我——”
大虎说着,瞪起涨红了的眼珠子,从腰里嗖地抽出一把捎谷刀,喀嚓一声戳在桌子上,震得桌上的灯火颤颤巍巍地晃动起来。
梁永生尽管从心眼里喜欢杨大虎这种直杆炮的性体儿,可他自己,毕竟是个心回肠转的人。所以他劝大虎说:
“先别!你就算豁上命,怕是也救不出长岭来!”
“旁人也这么劝我,我这才来找你,想让你帮我谋划个办法。”大虎缓了口气说,“我爹死在了他的手里,我儿这不又要死在他的手里——不管怎么拼,我决心是要跟他拼了!”
昏黄的月亮悄悄爬上窗角,正偷偷地朝屋里探头。屋外,风势猛了。庭院前头的杨树林子,好像在为大虎鸣不平似的,发出愤怒的吼声。
梁永生侧在被窝卷上,久久地不吭声,只是大口大口地抽烟。从他的鼻孔、口腔中喷出的黄烟,和从灯光上冒出的煤油烟子混杂起来,形成一片浓重的雾气,塞满了屋里的每一个空隙。这本来间量就不大的屋子,如今显得更窄狭了。这时,如果你没有注意梁永生那大幅度起伏着的胸脯子,你会感到他的感情平平静静,仿佛对大虎的境遇无动于衷似的。其实,梁永生目下的心中,既有对杨大虎的同情,又有对白眼狼的气愤;既有长岭被抓的新仇,又有爹娘屈死的旧恨。这些思绪一齐涌上心来,搅得他的心潮就像浩瀚大海又遇上了十二级台风似的,骇浪滔天,翻滚奔腾。只不过是他和大虎比起来,比较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罢了。
过了一阵,他可能是已经想出了营救杨长岭的办法,便把视线移到大虎戳在桌子上的那把捎谷刀上来了。接着,他拔下捎谷刀,紧紧地握在手中,朝大虎说:
“咱一定能把长岭救出来!”
“咋的个救法呢?”
大虎虽然这样问,可是他那紧绷绷的心弦,已开始松弛下来。因为永生的动作,实际上已事先给他做了回答。
梁永生笑了笑,把身子凑近些,就和大虎一字一板地谈起来。
屋后河水流动的响声,正在越来越大。它告诉人们:夜已深了。
大虎在炕帮上磕去烟灰,把安着青铜烟锅子的大烟袋往肩上一搭,又把捎谷刀插在腰带上,站起身说:
“就这么着吧。我走啦。”
方才这一阵,翠花和孩子们都坐在外间里听他俩说话,没进来。现在一听说杨大虎要走,杨翠花一撩门帘挡住了门口:
“杨大哥,住下吧……”
“不,住不下。”
“不住下也得吃了饭再走。”翠花指着热气腾腾的锅灶说,“我知道你饭量大,还特意多添了两瓢水呢。”
“不,家里这个烂蒲团,我得赶快回去。”
豁达的永生,理解大虎的心情,就说:
“不吃不吃吧。给大虎哥拿上个干粮,让他揣在怀里,路上饿了就啃两口垫补垫补。”
大虎走出屋门,志刚、志勇和志坚也齐打忽地围上来。这个拉住手,那个抓住胳膊,异口同声地喊“大爷”。杨大虎望着这帮虎头虎脑的孩子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在那潜伏着气愤的脸上,浮现出一天来不曾出现的笑容。是因永生的谈话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还是见了志刚他们忘了长岭?反正这时他的眼、嘴和鼻子,都有兴奋的表示。他望着这些茁壮的孩子动情地说:
“真是苦瓜长得大呀!你们跟着穷爹穷娘吃糠咽菜,也都长成硬棒棒的大小伙子了!”
“那一年,要不是大爷你救出尤大爷给我们送信,我们现在还不知怎么样了呢!”志刚话一落地,志勇又接上说:“要不是杨大爷给爹和奶奶送信、送盘缠,还……”
“你怎么啥也知道?”
“爹说的。”
他们像眷属重逢似的亲亲热热说了一阵儿,杨大虎就迈出院门走了。严冬是不肯轻易退走的:春夜的凉风,还在向人们显示着严冬的余威。在大虎和孩子们说话的当儿,永生回到屋里拿来一件破棉袄,披在大虎的肩头上。接着,他又和杨大虎肩并肩地迈着步子,说着话儿,一直把他送上运河大堤。在大虎高低让永生回去的时候,梁永生左手握住他的右手,右手搭在他的左肩上,又语重心长地嘱咐道:
“大虎哥,可千万别耍牛脾气呀!”
“放心吧。你方才说的那些话,我全记住了。”
“路上多加小心。”
“好。”
“进庄更要留神。”
“好。”
“劝劝你家大娘和大嫂子……”
“好。”
杨大虎大步一跨,踏着凹凸不平的河堤向前走去。一些砖头瓦片,在他的脚下骨骨碌碌地滚下河堤,跌入水中。
天空中,一疙瘩一疙瘩的白云块子,渐渐聚集起来,又变成了瓦灰色,土黄色……
杨大虎顺着长堤远去了,梁永生还昂首挺胸站在这高高的河堤上。风推浪涌,拍打着堤岸,也拍打着永生那颗剧烈跳动着的心。他那双像炮弹火光似的大眼睛,面对着灰蒙蒙、雾腾腾的夜空,面对着黄乎乎、死沉沉的原野,面对着正挟持着冰凌滚滚奔腾的运河,面对着正在被夜幕掩没着的杨大虎的背影,愣了老半天。
这时节,他正在竭力地想把那杂乱的思绪理出个头绪,认真地思索着问题,暗暗地下着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