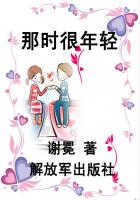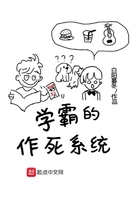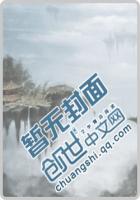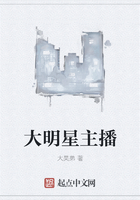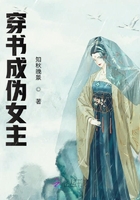梁实秋(1903—1987),原名梁治华,字实秋,出生于北京,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
1923年8月赴美留学,取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并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4岁。
他是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他笔耕不辍,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多达2000余万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代表作有《莎士比亚全集》(译作)等。
一
梁实秋所做最有影响的事,可能并不是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也不是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而是与鲁迅打了九年之久的一场论战。从1927年到1936年,两人围绕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翻译理念、文艺政策等诸多论题,展开了一场互有攻守的持久论战,直至1936年鲁迅不幸逝世才自然结束。这场论战给读者留下了100多篇文章,多达40余万字,以致后人编有《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一书,记录了论战的全过程。
这场论战乍起时,鲁迅已是当时中国文坛的巨擘,声名卓著,是文学界、思想界公认的领军人物之一,而比鲁迅晚来人间22年的梁实秋虽曾写过新诗,被称为“豹隐诗人”,但只是写过一些文学批评、初露头角的新人。当时,他毕竟是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24岁的小青年,知梁实秋者又有几人?可就在这有着极大反差的二者之间却展开了一场论战,二人真可谓是“忘年敌手”。
梁实秋的祖父是官居四品的清朝官员,父亲是首都警界人士,他也可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官二代了。梁实秋本人也很聪慧,13岁就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即今清华大学之前身)。在此期间,他与好友闻一多合作发表了《冬夜草儿评论》一书,得到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来信称赞。21岁时,梁实秋留学美国,后进入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师从美国著名人文学者白璧德,获得哈佛大学英文系哲学博士学位。梁实秋受到白璧德的影响很深,在他后来的著书撰文上也有意无意带着精英主义的烙印。大概也就是这种烙印,引起了关心普罗大众的鲁迅的反感。
鲁、梁后来的论战,主旨着重于两个问题,一是文学的阶级性和普遍的人性问题;二是关于翻译中的硬译问题。“丧家狗”事件,是这场论点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插曲。虽然论战中还涉及了其他问题,但基本都是论战过程中出现的附带问题了。
二
一般认为两人论战最初的起因是1927年梁实秋发表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但实际上在1926年,梁实秋在《晨报副镌》发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后,引起了文坛的关注,鲁迅于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校所作的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以及同年12月21日在上海复旦大学的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中,都已开始对梁实秋的观点发表辩难。同期有一个叫“徐丹甫”的给予了回应,评“鲁迅先生的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除此别无可称”,这个“徐丹甫”即是梁实秋的笔名。至1927年梁实秋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开始,双方正面论战正式展开。
梁实秋从美国回国之后不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又拿来重新发表了一次。文中,梁实秋再次把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其时,恰值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里。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问题是,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得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应该说,对文坛前辈鲁迅,他过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现在,他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尽管他十二分的不情愿。
文学和出汗[1]
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2]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胡涂”了。
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
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
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
听说,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那一种的命长,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
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
二七,一二,二三。
毫无疑问,如单就卢梭问题看,鲁迅是正确的。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还是对人类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伟大的卢梭都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的。梁实秋出于一己的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斥责卢梭,终致引起鲁迅的愤慨,正是理有固然。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显然,鲁迅不仅钦佩卢梭,而且表现出一种深厚同情。
但是,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度”。确实,在上列三篇杂文里,鲁迅的文笔是有些不大客气,像“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国开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绝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乎会使人感到极大的不舒服。因此,梁实秋在回敬鲁迅时,不可避免地也带上了意气用事的成分。
1930年,梁实秋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在文章中,梁实秋也不客气地写道,“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没有聪明才力的人虽然能侥幸得到资产,但是他的资产终于是要消散的,真有聪明才力的人虽然暂时忍受贫苦,但是不会长久埋没的,终久必定可以赢得相当资产。”“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
梁实秋的这篇文章一出来,很快受到了左翼文学理论家冯乃超的批评。冯乃超是广东南海县人,中国现代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他对梁实秋从骨子里弥漫出来的“贵族”气息很反感,当即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对梁实秋的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这是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文中甚至把梁实秋称为“资本家的走狗”,“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看到这篇文章后,梁实秋撰文《“资本家的走狗”》以示回复,文中不无委屈地辩解:“《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
“资本家的走狗”[3]
梁实秋
写完前一段短文,看见了《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一页起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阶级社会的艺术”,也是回答我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那篇文章的。《拓荒者》的态度比较鲜明,一看就晓得那一套新名词又运用出来了,——马克斯,列宁,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等等。但是文章写得笨,远不如鲁迅先生的文章的有趣。
这篇文章使我感得兴味的只有一点,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给了我一个称号,“资本家的走狗”。这个名称虽然不雅,然而在无产阶级文学家的口里这已经算是很客气的称号了。我不生气,因为我明了他们的情形,他们不这样的给我称号,他们将要如何的交代他们的工作呢?
“资本家的走狗”。那意思很明显,他们已经知道我不是资本家了,不过是走狗而已。我既不是资本家,我可算是哪一个阶级的呢?不是资产阶级,便是无产阶级了,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呢?查字典是不行的,韦伯斯特大字典是偏向资产阶级的字典,靠不住。最靠得住的恐怕还是我们的那部《拓荒者》。第六七二页上有一个定义(我暂时还不知道那里发售无产阶级大字典,所以暂以这个定义为准):
“无产者——普罗列塔利亚是什么呢?它是除开出卖其劳动以外完全没有方法维持其生计的,又因此又不倚赖任何种类的资本的利润之社会阶级。”这个定义是比韦伯斯特大字典上的定义体面多了,中听多了!我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了,因为我自己便是非出卖劳动便无法维持生计。我可不晓得“劳动”是否包括教书的事业,我的职业是教书,劳心,同时也劳力,每天要跑几十里路,每天站立在讲台上三四小时,每天要把嘴唇讲干,每天要写字使得手酸,——这大概也算是劳动的一种了罢?我不是不想要资产,但是事实上的确没有资产,一无房,二无地,那么,照理说我当然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了,我自己是这样自居的。为什么无产阶级文学家又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呢?假如因为我否认文学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文学家便说我是资本家走狗,那么,资本家又何尝不可以以同样的理由说我是无产阶级的走狗呢?也许无产阶级不再需要走狗了,那么,只好算是资本家的走狗了。
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的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经做了走狗,已经有可以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
梁实秋在文章中当然不仅仅是做辩解。只不过,他的反击更隐蔽,显示出绵里藏针的功夫,“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这段话的影射意味是比较明显的。
除此之外,梁实秋在后来发表的《答鲁迅先生》中继续影射鲁迅“通共”“通俄”“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这两段话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文章发表仅两年之前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一时间在全国上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在那之后,“通共”“通俄”就成了非常严重的刑事罪,直可判处死刑。梁实秋影射左翼作家“领卢布”,无异于借刀杀人。借谁的刀?当然是国民政府了。
鲁迅在看了梁实秋的文章后,决定亲自出手反击梁实秋,“来写它一点”。于是,被收入中学教材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华丽登场。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4]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5]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6]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7]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8],《晨报》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9],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一九三〇,四,十九。
针对梁实秋的辩解,鲁迅在这篇文章中继续猛烈攻击,“大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另外,针对梁实秋“领卢布”一说,鲁迅毫不客气地进行了反驳,“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鲁迅的这篇文章一出世,可谓一锤定音。以鲁迅后来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分量,从此,作家梁实秋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就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鲁迅和梁实秋此番论战的重头戏体现在一个“乏”字上,因为论战的深意已经超出普通的文人论战,而直抵敏感的政治神经。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和《“资本家的走狗”》两文中写出了暗指“左联”和鲁迅的三件事: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到××党去领卢布。梁实秋说:“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在白色恐怖时代,“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的时候,鲁迅认为梁实秋这种借刀杀人的影射“比起刽子手来更下贱”。鲁迅说:“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
鲁迅明骂梁实秋,实际上也在帮左翼“解套”,特别是最后两句用意非常明显:“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绝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言外之意是说,我们还是在文艺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论战,你梁实秋不能把文艺批评政治化,不要把国民党当局引进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乏走狗”的文章是一篇政治檄文,鲁迅这样的表述等于也给梁实秋留有余地。
写完后,鲁迅对自己这篇文章很满意。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写好这篇杂文交给《萌芽月刊》时,“他自己高兴得笑了起来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接着又说:“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在这次论战后,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手虽仍然时有发生,但那只能看作是一场激烈大战后的余波了。在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中,前前后后,两人你来我往的文字主要约有以下这些:
梁:《卢梭论女子教育》VS鲁:《卢梭与胃口》(1928年)
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VS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29年)
梁:《论鲁迅先生的“硬译”》VS鲁:《几条“顺”的翻译》(1929年)
梁:《“不满现状”,便怎样呢?》VS鲁:《“好政府主义”》(1929年)
梁:《文学与大众》VS鲁:《文艺的大众化》(1930年)
梁:《“资本家的走狗”》《答鲁迅先生》《鲁迅与牛》VS鲁:《“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1930年)
鲁:《关于翻译》VS梁:《翻译之难》(1933年)
梁:《病》VS鲁:《病后杂谈》(1934年)
……
三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鲁迅和梁实秋这两个论战当事人的预计。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梁实秋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与鲁迅的说法遥相呼应;1949年,解放前夕,梁实秋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后移居台湾。临行前,他对原暨南大学副校长王越说,“当年鲁迅要打的‘丧家狗’‘资本家的走狗’指的就是我……”
梁实秋离开大陆,对于他个人而言,是福是祸,倒也难以一语说清。不过,晚年的梁实秋在台湾创造了一大批作品,并且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
四
1970年,身在台湾的梁实秋发表了《关于鲁迅》一文,用相当大的篇幅回忆和评价这位当年的文坛论敌。文中写道:
近来有许多年轻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
在这篇文章里,梁实秋说,一方面肯定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说“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
“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
梁实秋在承认鲁迅的出类拔萃之后,又指出了他所认为的鲁迅的弱点,笔如刀,但却太过消极。或者说,在梁实秋的眼中,鲁迅是一个只发“不满现状牢骚”的人。所以,梁实秋说“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他希望鲁迅不仅发牢骚,还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找到一个解决不满意的“办法”。
曾经有人说从梁实秋的这篇文章里读出了“一代文豪、文界先辈的大度、风度与高度”,其实,梁实秋的这篇文章里是能读出一种天然的优越感的,这种优越感从何而来的呢?这大概又与梁本人的出身有关。正如梁实秋在他的这篇文章中所说,所谓“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他认为鲁迅的“怨恨之气”来源于他的“一生坎坷”。照这样的逻辑,那也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梁的所谓“大度、风度”也恰恰来自于他优良的出身、顺畅的人生经历。那么梁实秋本人逃出这个常理了吗?显然没有。而所谓的“文学没有阶级性”的观点、所谓的大度和风度,也就不过是出于一种阶级性带来的优越感而已。
更何况,历史的车轮在滚滚然向前进,每一个历史的重要时刻都有其最有价值的声音和风度。处在近百年前的中国,要改良还是要革命已经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抉择。改良主义,当然和所有想要当时的中国变得更好的社会改革方案一样,都有其积极和先进的一面,并不能全盘否定,但是,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中国已经到了非进行划时代彻底革新不可的地步,鲁迅文章中的所谓“革命性”,恰恰是那个时代沉疴已久的中国所需要的。当中国的历史进程已经在热血和抗争的曲折历程中行进到今天,知识精英们更不必仅仅因为当今时代的平庸、以所谓的普世价值而轻易否定鲁迅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