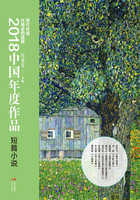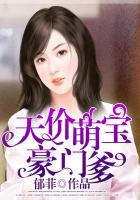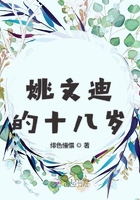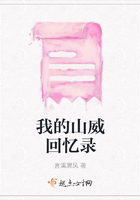其实,最能表现“外部研究”特质的,是“文学是人学”的张扬。就此而言,也可以说,中国学界从来没有完全抛弃或忽略过“外部研究”。
这本是一个老命题。它最早是由苏联作家高尔基提出来的,那是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事情。高尔基整个一生都在强调,文学应该始终高扬人道主义精神,高唱人的赞歌;文学要塑造、歌颂、赞美“大写的人”,要把普通人提高到“大写的人”的境界。总之,文学须以人为中心,不但以人为表现和描写的对象,而且目的也是为了人。这也就是他的“人学”的基本含义。联系到高尔基的全部创作实践,他毕生所从事的的确是这样一种“人学”的工作。文学是“人学”:这是作为一个作家的高尔基从自己毕生的切身体验中所得出来的令人信服的结论。作为伟大“文学”家的高尔基,也可以称为伟大的“人学”家。
曾经扭曲的历史
然而,在苏联的文学界、特别是文学理论界,并不是都对文学有这样清醒的符合它的本性的认识。有的人从“唯物认识论”原理出发,在说明文学与现实之间“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强调文学是现实的反映的时候,往往见“物”不见“人”。例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着名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开始,不少文学派别都反对写人,而主张写钢铁、写生产、写阶级、写生活事实和事业”。一些文学评论家指责高尔基的名言“人这个字眼儿多么令人自豪啊!”是“偷换唯心主义”,说什么“应该给文学提出的任务是:不是反映人,而是反映事业;不是写人,而是写事业;不是对人感兴趣,而是对事业感兴趣。我们不是根据人感受赖评价人,而是根据他在我们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对事业的兴趣于我们来说是主要的,而对人的兴趣是派生的……高尔基的公式:‘人--这个字听起来多么令人自豪!’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适宜的。”直到二十世纪四十、五十年代,仍然有人把所谓“现实”摆在文学的中心位置上,而“人”在文学中只被看作是反映“现实”的工具,只是从属性的手段。例如在苏联虽算不上第一流文艺理论着作却作为文艺学教科书出现的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中,就有这样的话:“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这虽不是权威的说法,却是流行的观点。恰恰是这种流行的观点,随着苏联文艺思想(包括季摩菲耶夫之类并不高明的甚至是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庸俗化了的二流文艺思想)向中国大量移植,也流行到中国来,并且与中国某些人的文艺思想一拍即合,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文艺理论中很有市场的糊涂观念。假如翻翻当时的文艺理论教材、着作和文章,几乎随处可见对文学反映和认识“外在现实”的强调,似乎文学的根本任务就是真实地反映和认识“外在现实”,而写“人”不过是为了写“现实”,“人”比起“现实”来反而成为次要的东西。这种观念把“唯物认识论”庸俗化了,当它在文艺学中贯彻所谓“唯物认识论”时,认为“物”就是“现实”,而“人”似乎可以和“现实”分开;“人”,特别是“人性”、“人情”,总是和“心”连在一起,倘若重在写“人情”、“人性”(“唯人”),就有点“唯心”的嫌疑;因而须“唯物”(“唯现实”)而不“唯心”(“唯人”)。这样,“唯物”固然是“唯物”了,也“唯”到家了,但却把“人”“唯”掉了,把“人情”、“人性”“唯”掉了,把“人道主义”“唯”掉了,把文学中最根本的东西“唯”掉了。这种观念也影响到创作,表现在某些糊涂作家(当然是些二流作家甚至是不入流的作家)那里,就是创作些“见物不见人”的作品,它们不是着重刻画人物,不是在描绘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性格特点上下功夫,而是着重描写生产过程、战斗场面,不是在“人”而是在“物”上使些蠢力气。理论上的这种糊涂观念和创作中的这种糊涂倾向,虽然一度流行,却一直受到真正懂得艺术、懂得文学的理论家和作家的抵制和批判。
钱谷融的功绩
正是针对当时文学理论中这种糊涂观念和文学创作中这种糊涂倾向,钱谷融在1957年5月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了一篇很着名的、也是长期受批判的文章《论“文学是人学”》。这篇文章着重批评了当时已经介绍到中国来并且在中国已经流行的前述季摩菲耶夫的观点:“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他说:“这样,人在作品中,就只居于从属的地位,作家对人本身并无兴趣,他的笔下在描画着人,但心目中所想的,所注意的,却是所谓‘整体现实’,那么这个人又怎么能成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自己的真正个性的人呢?”他发挥高尔基文学是“人学”的思想,反复强调:“文学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说文学的目的任务是在于揭示生活本质,在于反映生活发展的规律,这种说法,恰恰是抽掉了文学的核心,取消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因而也就必然要扼杀文学的生命。”在文学创作中,“一切都是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总之,人,才是文学的中心、核心。而且钱谷融还特别强调“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中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认为我们之所以对那些伟大作家“永远怀着深深的敬仰和感激的心情,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作品里赞美了人,润饰了人,使得人的形象在地球上站得更高大了”。钱谷融的这篇文章虽然不可避免地有着当时那个时代的历史的和认识的局限,但却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的最高理论水平。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第一,当某些人只注意“现实”而忽视“人”的价值、“人”的意义、“人”的作用时,他突出了“人”,突出了“人”在文学中的中心位置,并且响亮地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有的人说他曲解了高尔基的原意,或者说,对高尔基进行了“误读”。然而我认为,他并不是歪曲了高尔基,而是发展了高尔基,宏扬了高尔基,把高尔基那里还不那么鲜明的命题变得十分鲜明,把高尔基那里还没有直接连在一起的那几个字直截了当地连在了一起:“文学是人学”,使文学理论中这条千古不灭的真理更加显豁,从而也使高尔基更加光辉、伟大、可爱。如果这叫做“误读”,那么,“误读”得好!第二,当有的人糊里糊涂地把文学中的人和现实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并且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弄颠倒(“现实”为“主”、“人”为“从”)时,钱谷融指出,在文学中,“现实”就是人的现实、即“人的生活”,并且把颠倒的关系又颠倒过来:“人和人的生活,本来是无法加以割裂的,但是,这中间有主从之分。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反过来,你假如把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生活本质,作为你创作的目标,那么你不但写不出真正的人来,所反映的现实也将是零碎的,不完整的;而所谓生活本质,也很难揭示出来了。”第三,钱谷融突出强调了“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灵魂:人道主义精神。这是他对中国和外国优秀文学中人道主义精神的继承,特别是对“五四”以来倡导“人的觉醒”、“人的解放”,提倡“人的文学”的优秀传统的继承。当然,那时他还没有象后来人们明确区分所谓“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但他强调“尊重人同情人”、“把人当作人”,绝对比后来(特别是“文革”中)某些人“把人当作兽”或“把人当作神”要进步,要正确。第四,钱谷融注意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注意文学自身的特性。当人们只看到文学的“认识”性质、“反映”性质,把文学的任务只局限于“揭示”“本质”、“反映”“规律”时,他提醒人们要注意“文学作品本来主要就是表现人的悲欢离合的感情,表现人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对于不幸的遭遇的悲叹、不平的”;当人们观察文学的眼睛只盯着“外在现实”、“客观生活”时,他提醒人们要注意人的内在精神、情感世界-不但要注意作为文学创作对象的人,还要注意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人(作家)和作为文学批评主体的人(读者与批评家)的内在世界、世界观、思维和情感方式:“不仅要把人当做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还要把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作为评价作家和他的作品的标准”,“在文学领域内,既然一切都决定于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那么,作家的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了”。这潜伏着后来(特别是1978年以后的新时期)人们摆脱文艺学中单一模式,从多种角度观察和阐释文学的萌芽;也成为后来“主体性”文学思想的先声。
一幕悲喜剧
然而,这也仅仅是潜伏的“萌芽”和微弱的“先声”而已。无情的现实是,钱谷融的这些文学思想一直处境悲惨,被加上各种罪名予以批判。政治上扣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的帽子,我们不去说它;我们现在着重从学理上看看这种批判所透露出来的的“意味”。它表明,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学重“物”而轻“人”,重“外”而轻“内”,重“客观”而轻“主观”,重“客体”而轻“主体”。它忽视了文学的对象根本上是“人”;忽视了文学的特性之一就是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挖掘、表现和描绘,是对人的灵魂的塑造、改造和创造;忽视了文学正是通过影响人的灵魂、影响人的精神世界来于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的;它忽视了作家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这无疑是重大的理论偏颇。这种偏颇直到1978年结束了左的思想路线之后才逐渐得到纠正。于是,有了80年代“文学是人学”的再度张扬。
这首先表现在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这篇长期受批判的论文,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一本理论着作出版发行。这等于把它郑重其事地重新发表了一次,一是表示理论界对这篇文章基本观点的认同和赞扬,二是为它平反。在这前后,一些报刊杂志发表了钱谷融的与此文有关的文章,如1980年第3期《文艺研究》发表了他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这是《论“文学是人学”》受到批判后,作者于1957年10月26日写的一篇检讨性文章,而其内容,则是对自己观点的进一步阐释和辩护。1983年第3期《书林》又发表了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说明该文写作、发表和受批判的一些情况,提供了一些背景材料。这些着作和文章的发表,说明当时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其次,许多学者着文,进一步阐发“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例如吴元迈和李辉凡都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高尔基当年有关文学是“人学”的思想,及提出这个命题的文化思想背景情况。特别是,他们对文学是“人学”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理解。吴元迈说:“文学是人学。更正确地说,文学是艺术领域的人学。因为在世界上除了文学以外,还有心理学、生理学、解剖学……也是研究人的,它们都属于人学的范围。我们只有把文学看成艺术领域的人学,才能够深刻地揭示出它的特殊本质和特殊意义。”包忠文在《试论艺术规律和“人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我们不能满足于‘文学是人学’这个一般的结论,应当在此基础上向前跨进一步。这就是说应当进一步研究作为;‘人学’的文学和各种研究人的科学的不同点,研究文学意义上的人和各种科学意义上的人的不同点。”他进一步阐释说:“作为文学意义上的人,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立体的、社会的心理结构,而非简单的、单线条的、机械的平面结构。我们承认文学意义上的人的灵魂的复杂性,同样也应当承认在这个复杂的整体中,有其主导的方面,正是它构成了人的全灵魂的核心。正是这个主导方面,使人的灵魂中的各种因素,得到有机的融合,并构成活生生的艺术上的‘这一个’。”
李劫在《文学是人学新论》(《艺术广角》1987年第1-2期)中说,“文学是人学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意味着相当具体的规定:对人的规定,对文学的规定,对文学是人学的规定。也即是说,在这个看来空泛的概念之下,显现出了许多生动实在的内容。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文学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文学。而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则意味着一种人类的自我生成过程。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是文学向人的生成,一是人向文学的生成。前者具有文学的人本性,后者具有文学的文本性,它们构成文学与人的双向性,即人在文学创造活动中创造了自身,而文学又在人的自我创造过程中获得了存在。相对于人的存在,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显示了它规定性,而相对于文学的规定性,人作为文学的创造主体在一个非人化的世界面前得以确立了自身。文学与人之间这种相应的创造性构成了彼此的同构性,即人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创造而创造自身,语言艺术通过人的自我创造而体现自身的文学性。前者构成文学的审美性质,后者构成文学的审美样式”。
李劫在这篇论文中反复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虽然略嫌抽象,但他的意思还是具有启发性的。刘再复在《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中强调,《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几乎是不待论证的,“这一命题的深刻性在于,它在文学的领域中,恢复了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地位。由于感悟到这个命题的内在意义,作家把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中心,天才地再现了人类在历史舞台上的各种行为”;他还从三个层次上深化“文学是人学”的内容:一是文学是人学的含义“必定要向内宇宙延伸,不仅一般地承认文学是人学,而且要承认文学是人的灵魂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二是强调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深化,“就不仅要承认文学是精神主体学,而且要承认文学是深层的精神主体学,是具有人性深度和丰富情感的精神主体学”;三是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深化,不仅要尊重某一种精神主体,而且要充分尊重和肯定不同类型的精神主体。
“因此文学不仅是某种个体的精神主体学,而且是以不同个体为基础的人类精神主体学,正是这样,文学无法摆脱最普遍的人道精神”。
总之,研究文学,既是“外部”的,也是“内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