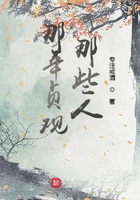这时候的鲁迅确实有点失控,他几乎是逮谁骂谁,施蛰存、陈其昌、徐懋庸都挨过他的骂。包括梅兰芳,他骂他“不男不女”,扮相像“麻姑”。也包括王国维,骂他“老实得像火腿”,连赛金花这样的妓女也不曾放过,不仅嘲讽她“早已被奉为九天护国娘娘”,还歹毒地讥笑她与“德国统帅瓦德西睡过一些时候”。当然,鲁迅骂得最多的还是新月派诸君,那句著名的骂人话“痛打落水狗”其实是骂梁实秋的,这一令无产阶级痛快无比的名骂一直流传至今,并且这一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被多次选入不同类型的教科书中,成为鲁迅的杂文代表作。
鲁迅与梁实秋的这场论战旷日持久,留下太多的学术商榷空间。最后左联的评论家冯乃超也像程咬金一样半道杀出,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中说:“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自己认定自己是站在大众这一边,凭空就站到道德制高点上,凭空就生出自豪与优越感来,不过是逞一时口舌之快而已。梁实秋在《新月》上回复了一篇文字《资本家的走狗》,据冯雪峰回忆,鲁迅看到此文后连声说:“有趣,还没怎样打中他的命脉他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什么用的走狗。”鲁迅决定自己再来应战,很快一挥而就写成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这一次的“痛打落水狗”让鲁迅十分开心,《“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也写得相当有力量,大量的政治词汇有浓烈的左翼色彩,这种色彩在新中国成立后铺天盖地,所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根本不陌生。争论双方都将自己从潜在的政治迫害和裙带关系中解脱出来,不惜意气用事,甚至实施人身攻击,使得论争的本来面目越描越黑,最后完全遮蔽学术目的,致使双方感情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这不是左联与新月派的第一次交战,也不会成为最后一次。在这之前,鲁迅其实多次有意无意地以笔当刀,将锋利的锋刃对准那轮“新月”,在《各种捐班》、《拿来主义》和《文坛登龙术》等多篇文章里,将新月派骨干邵洵美骂得狗血喷头:
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纹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应该代以电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为这才是新时代的美术。“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而“文学家”或“艺术家”也就这样的起来了。捐官可以希望刮地皮,但捐学者文人也不会折本。印刷品固然可以卖现钱,古董将来也会有洋鬼子肯出大价的。
《拿来主义》其中一段话:“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
这些话让被人称为“文坛孟尝君”的邵洵美耿耿于怀,他对鲁迅一向尊敬有加,那次自己出钱请萧伯纳在著名的功德林吃素斋,还请来宋庆龄和鲁迅一同作陪。临走时因为下雨,鲁迅站在屋檐下淋得直哆嗦。那是邵洵美第一次见到鲁迅,主动请鲁迅上车,一直将他送回家。他当然记得鲁迅对他的谩骂,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关进提篮桥监狱,还没有忘记这回事,向他的狱友贾植芳先生交代,务请他出狱后帮他澄清几件事,其中之一就是告诉大家,他邵洵美所有的文字,并非鲁迅所说的“请人代笔”,全是他一字一字抠出来的。他没好意思说,鲁迅说他是个“穷青年”,他的财产是“做了女婿换来的”。其实他是名门之后,上海道台之孙,他的家完全与他太太家——盛宣怀家族平起平坐,鲁迅骂得毫无根据也毫无道理,就如同他早些时候骂林语堂、徐志摩一样,其实都没有什么大错,只是他看不惯他们身上的欧美习气,或者更看不惯他们与胡适的哥们义气,就要抡起大棒“痛打落水狗”,就要“一个都不宽恕”。正是因为鲁迅身上这种战斗倾向,才让他走进毛泽东的视野,因为“痛打落水狗”就是毛泽东的“宜将剩勇追穷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