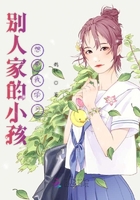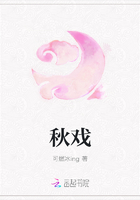久客还乡,风吹百草,漫漫长道上,是一颗早已经老去的心。可以不可以,还有一种尘世的熙光,温暖我的余生?
回车驾言迈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这是一首警策自己的诗。
讲述了一个久客还乡的行人,驱车跋涉在漫漫长道上的所见所思,以及对自己的自警和鞭策。
他见到什么了呢?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见到的是遥远的路途,漫漫的长道,是四野茫茫的空旷,是风吹动着百草向旷野的深处倒伏。
这本是春季,草木荣生,该是一派生机,春光潋滟的。可是我们分明感受到的是一种凄清和苍茫。这有点像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个有声有色的春天的郊野,先出现的是一个点——车,然后是一条大道——长道,接着整个画面充满了四野的空阔,最后是画面下方的物——草,春风中,百草丰茂,摇曳有声。
极是喜欢这句“东风摇百草”,有人说,这是指春风吹生了百草,如果这样去理解的话,“摇”的情味就失掉了,草木于风中摇曳之美,也宛若一个妙龄少女晨起梳妆时,自然而然的顾盼之态,蓦然叫人心动。更何况,这里的“摇”不仅是草木之“摇”,更是诗人内心之“摇”,体现的是诗人神思摇曳之情状。
前人评论这个“摇”字为“初见峥嵘”,唐代的诗僧皎然在他的《诗式·十九首》中云:“《十九首》辞精义柄,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我不知道皎然是针对十九首里的哪个构思说的,想必也是包括这个“摇”字的。
《诗经·黍离》里面也有个“摇”字,同样是写行人的,同样是草木引发了行人心头的伤悲。
《诗序》里说:“《黍离》,悯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周宫室,尽为禾黍。悯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
就是说诗的主人公是东周王朝的一位大夫,东周末年,他来到曾经是西周首都的镐京,只见往日辉煌巍峨的宫殿,繁华热闹的街市,乃至熙熙攘攘的人群都已经不见,眼前只有一片茫茫原野,长满了黍稷禾苗。风吹来,黍稷青青,禾浪阵阵,大夫不禁悲从中来,忧伤不能自已。
所以“行迈靡靡,中心遥遥”,步履沉重,内心神思摇荡,愁怨难消。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理解我的人,知道我内心的忧伤,不理解我的人,还以为我在寻找什么。
这个大夫在“忧”什么?西周的灭亡是由于周幽王残暴无道,当时,关中地区“三川竭,岐山崩”,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大地震,之后又是波及全国的大旱灾,周幽王却倒行逆施,“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任用谄媚好利的虢石父,宠爱美人褒姒。
更可气的是,周幽王“肯爱千金轻一笑”。妃子褒姒不爱笑,虢石父便献计,叫周幽王点燃各烽火台上告警的烽火,于是,各诸侯王匆匆带兵来救,结果是一场玩笑,褒姒开心大笑,幽王说:“妃子一笑,百媚俱生,这是虢石父的功劳。”立刻赏给他黄金千两。
等到诸侯王联合少数民族犬戎来犯,烽火点燃了,却再也没有诸侯来救了。西周灭亡,幽王被杀于骊山。
这和商纣王残暴荒淫,被周武王消灭何其相似啊。
幽王不记殷商灭亡之痛,重蹈殷商的覆辙,导致身死国灭,当初的繁华笙歌,终于只剩下这些黍稷青青了,怎不令人“中心遥遥”乃至“中心如醉”、“中心如噎”,忧伤、沉重乃至内心哽噎难语。
黍稷不知家国悲,春来犹离离,惜人心不似草木,兴衰不动。
后来,“黍离”之悲,就成了家国之悲的代名词。
人心是最不堪昨宵触目所见的荣衰兴败的。
刘禹锡有一首《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据说写这首诗的时候,刘禹锡根本就没到过南京,那时,他在做和州刺史,南京只在遥望中,他是在一个僻静的小城里,根据自己的想象和阅历,写下的千古名篇,和李白的那首《登金陵凤凰台》的前四句“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怀古伤今的。
不过,这“乌衣巷”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宋张敦颐撰《六朝事迹编类》卷之七“屯舍门·乌衣巷”条。原文是: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为业。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见一翁一妪皆衣皂,引榭至所居,乃乌衣国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归,复乘云轩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栖于梁上。榭以手招之,即飞来臂上。取纸片书小诗系于燕尾,曰:“误到华胥国里来,玉人终日苦怜才。云轩飘出无消息,泪洒临风几百回。”来春,燕又飞来榭身上,有诗云:“昔日相逢冥数合,如今暌违是生离。来春纵有相思字,三月天南无雁飞。”至今岁竟不至。因目榭所居为乌衣巷。
王榭恋乡不愿再去乌衣国,玉人思念,空自相思,才有这乌衣巷。这到底是传说,世间很多的传说都不可信。
但是,这里确实是东晋的王导和谢安的居所,他们前后为相,撑起了东晋的江山。尤其是谢安,风流雅量,世所不及,前三十年潇洒随性地隐居东山,后三十年轰轰烈烈地出山。是东晋的一笔华章亮彩。
乌衣巷里居住过很多名士,书圣王羲之、山水诗鼻祖谢灵运、谢洮也住在这里,另一个江南氏族、才兼文武的纪瞻也“即家开府乌衣巷”。
王、谢家族,在这里一住就是三百年,演绎了多少的繁华盛事。到了唐代,经过隋朝的“平荡耕垦”,六朝帝都的繁华过往,不过只剩下些“夕阳”和“古丘”罢了。
人事沧桑往往就在兴衰不言中。
九州何处无兴衰,人间何时不兴废?人常常却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姜夔也有一首《扬州慢》,在他的词前小序中写道:“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
扬州自古繁华,但经历了南宋的战火之后,也是“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金兵的铁蹄,使得扬州也只剩下荒废的池塘和高耸的古树了。
最喜欢那一句“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繁华不再,二十四桥仍在,波心里,只有冷月,人心呢?怕有太多的不胜今昔之感吧!就像一幕好戏的落场,人散去,空荡荡的,只剩下寂静。
当初杜牧在扬州写下“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年少轻狂,写下“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自嘲,杜牧的诗里暗藏着扬州繁华的过往,可是,写《扬州慢》时,姜夔也不过才二十二岁,也是可以和杜牧一样肆意轻狂的年纪,却为什么,扬州的繁华却给了他如此的哀伤呢?
昔盛今衰,六朝的兴亡,都如一梦,梦醒来,“波心荡,冷月无声”,人世沧桑往往就在不经意的一瞥中。
物皆无情,不管人世悲欢。但万物有灵,人类与大自然总能搭起一条神秘的通道,丝丝缕缕、若有若无地相呼应。
十九首里,百草也似无情,在东风里,在历史的深处倒伏,这一“摇”,“摇”出的不是历史的兴亡之叹,它只是一个行人内心的苍凉和忧伤。犹如风中百草,摇荡不已。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东风里的百草早就不是曾经遇见过的“故物”,早已经不知道几度寒暑了,季节的转换如此之快,怎么不叫人变老呢?
这里面,包含着诗人数载的蹉跎,这正是感到内心悲怆的根源。所以,这里老去的也不仅是年岁和容颜,更多的是士子漂泊求宦的心。
《世说新语》里有一则里说: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最佳。
王孝伯也是东晋著名的美男子,唐代的诗人徐夤写过“三五月明临阚泽,百千人众看王恭”,说王恭此人如明月朗朗,风采出众。这王恭就是王孝伯,他名王恭,字孝伯,《世说新语》常常喜欢用表字、名号和官职来说事,比如王导是丞相就叫王丞相,殷仲堪当过荆州刺史就叫殷荆州。
王恭不论走到哪里,都惹得千百人围观,回头率相当高。《晋书》里说他“少有美誉,清操过人”。容貌美好,时人称赏他“濯濯如春月柳”。他曾经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这个人是性情中人,《晋书》本传中说他“恭性伉直”,“暗于机会,自在北府,虽以简惠为政,然自矜贵,与下殊隔,不闲用兵,尤信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