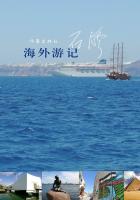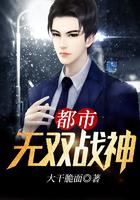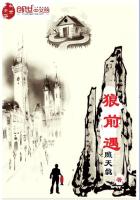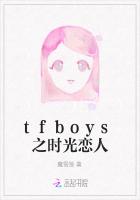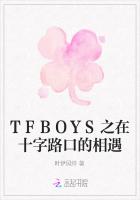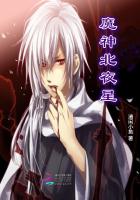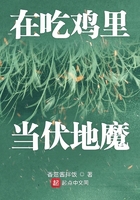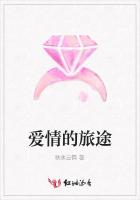“语言中”的主体
——《诗的晦涩》辨析
纪 梅
从当代诗歌史的脉络来看,对语言的强调既始于“朦胧诗”又始于对朦胧诗的反叛。语言与主体性的论争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初露端倪:其中不乏渴望占据某种想象的诗歌史地位所导致的命名冲动、游戏性和运动性的“英雄出演”;对“朦胧诗”较有文本价值的反思则来自于一些诗人实验性的文本探索。这一探索既源于“影响的焦虑”,也来自对诗歌技艺的推崇。“后朦胧”诗人——包括1984年以后的北岛、多多、杨炼等人——的反思主要集中于“语言和言语”问题上。在他们看来,面对独断性的权力意志和“集体话语”,朦胧诗以反讽方式说“不”的姿态,与官方话语构成了尽管针锋相对然而又彼此依存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国诗歌有限的光明习惯性地依附于广大的黑暗”(西川);“它太滞泥于正确性”(张枣)。对于“后朦胧”诗人来说,“先锋,就是流亡”(张枣);且这种流亡不是身体和精神的流亡,而是“词的流亡”(北岛)。
一、语言中心论的流布和主体性的“黄昏”
伴随着语言哲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西方后现代主义所盛行的“作者之死”、“人之死”等观念的传入,主体性观念刚刚苏醒,便被裹挟于喧哗与口水之中,命运叵测,前途未卜。随后,中国诗坛开动了“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张枣)。主体性写作逐渐让位于文本自足的游移;对峙的、杂糅着历史反思和批判的写作逐渐让位于低语的、私人的、充满想象和超验的“书房话语”;“言志抒情”的抒写主体减缩为纯粹修辞性的“你”“我”:“此时你制造一首诗/就等于制造一艘沉船/一棵黑书/或一片雨天的堤岸”(柏桦:《震颤》);“雨中的马也注定要奔出我的记忆/像乐器在手/像木芙蓉开放在温馨的夜晚/走廊尽头/我稳坐有如雨下了一天”(陈东东:《雨中的马》)显而易见,诗中所描述的沉船、黑书、堤岸、乐器、木芙蓉等都属于诗人未见之物,属于非经验的世界。缘于“制造一首诗”的修辞虚构性——“诗”在这里实体化了,就像“沉船”与“黑书”;作为主体的“你”“我”,不是诉诸于在场、感受和饱含主体感性的描述,而是隶属于修辞功能或话语功能的安置。
柏桦、陈东东等人的诗歌代表了上世纪80年代先锋诗歌向“词的流亡”的转向,这是一种将语言奉为本体的诗学观念。对语言“纯洁性”和“先锋性”的渴望,一方面源于诗人对集体话语和极权性质的众口一辞的厌恶和抵御,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西方文本的模仿和学习。因此,在80年代初中期的文本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军舰鸟”、“灰知更鸟”等明显的西方物象。从根本上说,这类诗歌忽略周围的世界、经验、感知和真实“所见”,同时略过与之相随的社会历史观念、理念和意义,从而将雅克布逊式的“语言的突出”、罗兰·巴特式的语言的欣悦和结构主义的文本的自足性作为写作的诗学功能或诗学效果。这是一种“元诗”或“诗歌的形而上学”,它服膺于语言本体和形式本体的观念:语言不应仅仅是一种表达观念、承担意义的手段和媒介;对“意义”和“思想”的言说不再是写作的正当性目标,修辞活动以及写作所构成的文本自身才是语言活动的指归;真正的诗歌就是语言内部和形式自身的言说——从“诗乃语言创作,仅此而已”(让·罗耶尔)至“诗到语言为止”(韩东),只改动了几个不重要的词而已。当语言的超现实和魔幻化替代了对现实的具体指涉,诗人的主体性或被悬置,或退隐于语言的背后。
相对于中国诗学开始于80年代中后期的主体性隐退以及语言主体论的转向,西方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开始了追求“纯诗”这一颇为形式主义的文本欢乐的旅程。强调主体性与批评意识的马塞尔·雷蒙在分析了包括马拉美在内的象征主义诗歌之后曾提醒人们注意,“绝对的纯诗只有在人世间以外的地方才可能想象。它只能是非存在。……对于诗来说,这种非存在的诱惑是十分可怕的危险”,“因为千真万确的是,诗歌更多的是从生活以及对生活而不是对语言的思考中获得滋养。”如果回到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学说的话语现场,我们或将更为惊讶地发现,中西方在对语言主体论的推崇上存在着多么大的“概念的年代误置”(耿占春)。
受尼采的身体哲学和索绪尔的语言哲学影响,关注意识和理性的主体哲学在19世纪末开始遭到大规模的质疑与攻击,并在20世纪席卷了包括宗教神学、语言分析、系统论、结构主义等多个领域。语言哲学通过将语言抬升到主体的位置从而宣布“作者已死”。其主要观点认为,世界是通过语言来建构、塑形的,语言是第一位的,主体不过是在语言中预留一个位置,而行动中的人将在语言中消失:“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在“反人道主义”强大的号召力和反抗之下,主体性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黄昏”。
总的来说,当代西方对于主体主义的攻击“其实大都只是对自我主义(egoism)、自我论(egology)、意志主义和主体这个概念的批评”;结构主义等学说也并非反理性,而“仅仅是关于部分与整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对关系的重新调整”。如人们在认识论的历史上曾经过于依赖“宇宙规律”、“逻各斯”等等“真理”法则一样,“语言主体论”则是另一种改头换面的逻各斯和观念膨胀。德里达意识到,对“语言”一词的贬低本身以及我们对它的崇信,“暴露出对时尚的被动屈从、暴露出前卫意识,也即无知……‘语言’这一符号的膨胀乃是符号本身的膨胀,是绝对的膨胀,是膨胀本身。”
在言及主体性的基石——即先验的“我思”传统遭遇结构主义挑战时,利科写道:“从现在起,整个我思传统所诉求的这种主体定位,必须在语言中,而不是在语言旁侧加以操作,否则就可能永远无法超越符号学与现象学的二律背反。必须让这种定位在话语要求之中,亦即在语言的潜在系统据以变成为现实的言语事件的活动中显现出来。”在自我与“世界”之间,利科认为语言“既不是基础,也不是客体”,而是“媒介”、“中介”、“中间”。正是在语言中并且通过语言,“主体才为自己定位,世界才彰显自己。”
相对来说,虽然中国传统文学并不缺乏个人性的、主观性的感受和经验,亦不缺乏主体性的意志与精神,但是这种主体性感受并未得以经常性地、持续性地在积极的、备受鼓励的环境中进行自由地成长和展现。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主流和制度建设中,个人主体或消隐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国家主体性之中,或消融于“悠然见南山”、“相看两不厌”的“天人合一”中怡然自得(在古典****制度下,这或许是一种高妙的生存哲学)。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影响,主体性观念和个人意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一次爆发性的苏醒。然而,仅过二三十年,“救亡”就压倒了“启蒙”;进而,权力话语和集体意识彻底湮没了个人话语……这一情形直至70年代末“朦胧诗”的出现才有所改观。基于此,中国学界于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之后向语言中心论的急剧转型,并非如西方思想语境中观念逻辑的纠偏和调整,“而是一种充满断裂感受的改变,其中包含着自我意识的断裂与非连续性”。语言的“纯洁”和“先锋”在80年代如若还能天然成为一种道德探险或不无想象性的伦理承担,1989年之后,继续将“意义”和“思想”托付于语言的演奏或语言的狂欢,已难以规避经验世界被语言覆盖、社会历史语境被语言享乐主义所篡写的危险。对于十年前刚刚开始写作的诗人来说,80年代末社会断裂式的巨变让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的青春理想如何被巨大历史事件的尘埃所湮灭——包括“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说话而非诗人言说”之类的语言本体论神话理应作为这次失败的殉葬。此时涉及的与其说是艺术和风格,不如说关乎行为、生活、真实的经验,自我的认识与塑造。马塞尔·雷蒙曾感叹说,对美的绝对崇拜与对文字的偏好对19世纪末的象征主义者造成了不小的损害。后者的“典型态度”是“躲避于自我之中,将目光转向自身,为的是满足青春与消极完美的欲望,或者出于对生存的某种恐惧、厌倦、厌恶,在大多数情况下带着迎合自我的全部内在变化的几乎恋人般的欲望”。1989年之后的中国学界对“纯诗”的钟情或有着更为复杂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语言本体论的继续流布趋势意味着一种相反方向的逃逸,稍显悲观地猜想,或出于避居式的、明哲保身的生活策略,或不自觉地堕入一种匠人式的自欺,前者导致写作失去思想力量和感知的有效性而苍白无力,后者则使写作沦为华丽、精巧而乏味的词藻堆砌游戏。“有如语言蜕化为诗行,慨然献出了/意义的头颅。”(陈东东:《眉间尺》)最早进入“纯诗”写作的陈东东已对“语言蜕化为诗行”这一行为的意义提出了自我质疑。张枣也意识到,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对元诗结构的全面沉浸使其参入了“诗歌写作的环球后现代性”,也使其加入了它一切的危机,“说到底,就是用封闭的能指方式来命名所造成的生活与艺术脱节的危机。”而它最终将导向“身份危机”。“可以说80年代末是一种结束——它大致上标志着一个看似在反叛实则在逃避诗歌的道义责任、看似在实验实则绕开了真正的写作难度的诗学时代的结束。”是的,“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那些“被限制在过于狭窄的理解范围内的纯诗写作”同样“失效了”。
在抽象主体和语言主体论的幻觉双双破产之后,写作者需要在语言与主体性之间寻求一种更能体现、表达自身境遇的关系和方程式——这将是越过了追赶新奇、时尚、潮流的青春期性格的“中年写作”或写作的“晚期风格”:一方面,主体必须通过一种中介的迂回才能认识、定位和安放自身;另一方面,诗人面对着一次真实意义上的语言学转向,寻找或锻造出另一种语言,一种可描述自身切实经验,可体现自己生命的某种东西,理想情况下还能帮助诗人明晰自身社会历史处境、发掘社会历史意识深度的语言。这是一种“可见性”的语言,一种从词语自足的迷醉中逃逸并恢复话语与社会历史语境深度关联的语言。
主体、理性和认知从来都不是语言和修辞的敌人,相反,是“英雄出演”的渴望和不加反思的激情给集权主义提供了远比宣传和恐怖更有力的支持。当历史事件、政治语境、给定的生存作为一种先在困境,诗人与批评家只能无可选择地在伦理观念、道义责任与个人的自由意愿和文学的自由表达之间反复角力。基于此,本文试以描述和分析1989年以来的诗人与诗学批评家如何在“语言中”平衡历史意识、历史记忆、伦理教化、情绪、感受、知觉、他者等力量,从而明晰、确立自己的主体性,进而兼至技艺的完善和写作的合法性。
二、感受性主体或悲悼的诗学
我们怎能写作?
当语言无法分担事物的沉重,
——王家新《瓦雷金诺叙事曲》
这是1989年冬,“事物的沉重”已击破“语言”的神话,诗人陷于错愕、失语和痛苦的哀鸣中,“写作”也陷于某种困难和不可能。同王家新一样,耿占春写于90年代初的思想札记中也出现了很多噩梦:从“发射自我”到“机器兽”,从“乌有城”到“地狱”,这个最早的语言主体论者此时正处于最深重的沮丧和痛苦中。语言不可能再作为“一种纯粹的主体”,“我思”的抽象主体和绝对的自我意识同样显得可疑:“世界的存在依赖于我的主观性?……你既然有这么了不起的主观意念,那为什么还怀着一种难忍的忧伤,怀着一颗难以抑制其颤抖的心躺在这里,对一切都如此感觉束手无策呢?”(耿占春:《窗外》)
沉重、忧伤、对一切感觉束手无策……这正是受损的现代主体的主要特征。1989年之后,“主体性的缺失”越发成为普遍困境:他会是一个认识主体、感知主体、情绪主体,甚或成为一个“半自主”的道德主体、“半自由”的经济主体……然而却不是一个政治主体和行动主体。就像在昌耀等人那里所显示的,一个人可以因为良知与勇气而成为“一个内在道德的主体,至少是一个悲剧式的道德主体”,却很难成为“有效的道德主体”。主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被动地承受难以抗拒的社会机制施加于自身的力量”,个人的主体性“多半体现在对自身悲剧命运的感受能力中”: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
——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
主体在审美化的感受性(“写作”)与行动力方面(“生活”)的不对称会导致分裂感和挫败感。弗洛伊德在《悲悼与忧郁症》中曾指出,“对失去对象的忧郁依恋不仅仅限于被爱恋对象的丧失,也包括某个地方、共同体甚至理想的丧失。”这种丧失或将主体带至极端的负面情绪之中:
然而我越来越愤怒。
一天比一天愤怒,一秒比一秒愤怒。
为这些谎言,为这些柔软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