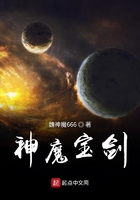第四三七章盔甲
蒋涵子勾画石雕像。靛君境已经没有了:蒋涵子私著恩怨留下的任何目的刀。
无欲成刚。靛君疯狂毁灭的就是——被定义固化成的过往概念、观点。御风鲜活的灵动,蒋涵子一颗生动起来的心,已经断然走脱——意识形状的古纪。
靛君依旧沉湎于自以为然的刀墨战,舒服于自戕的烟云,盘亘于自侍灵感杀伐的意境当中。暂无所知。
瞬间凝定的蒋涵子,已经是春令鲜光与和风下——大自然的野性灵虫。
一纤笔动,万灵贲生。
蒋涵子的铅华,在直锐的精致笔端,第一次接纳了光感与色素的张力。
因为精致形格本来就含有密叠巧筑的方寸,立体驻形于时空,再赋予光感锐直穿梭的鉴辨与判断,在石像上生成多角度细节的观感。蒋涵子和谐的心态知觉中,一蹙紧缩的立体,已经显化生命形绽的快意。
已往那些平均力量线条的勾勒,此时,也可以表现不同力感下的虚实与浓淡变迁。
这些精致微弱的细节,更让形格豁现丰满生机。
簌簌笔动,画境蓬张。
时空云辇与大地,在灿烈光焰中,高驻造化境各种形格矗直的壁垒。亘古空间,不假任何写意的旷朗光线,显示大自然境原初的本色。
依赖原初状的宏阔背景,蒋涵子素笔下,忽然呈现:石像背景“唤”出的古老苍生群。
不断随蒋涵子画笔添著进恢宏境的背景,情味表现的色彩,结合明暗变迁的光感,瞬间焕发万化生机——变作造化下活过来的一个个丰满实躯。
原来,写生一尊石像,素光与素色竟然同步携带出:背景无限的造化众生相。
百千万万种形状,不仅是坚硬如铁的图腾,而且包含了百千万万种明暗交织的情味。
密叠浮雕般丰隆的立体背景中,石像敛祍微小的含蓄,却是憾然拉动无尽背景风声的统御。
随敛形,繁密布陈的细微皱褶,包含着无群握控的力量和皈依统宗的方向。
蒋涵子虽然仅仅写生一尊石雕,却料,步步惊笔,背景显著的相越来越多。
蒋涵子的笔格,写意虽然变得温柔泰和。但精致线条带动的素光与素色,让落点的每一笔都“站”成一个饱满逼真的立体。
那种笔法,就是靛君未曾经历过的形格刀。
靛君依然站在画境中,身后飘逸着刚刚一番刀战残留的风烟。整个人,仿佛古战场单独活下来的一介枭雄。
似乎突然惊醒:蒋涵子临境的温柔写意,不再是单纯的平面画。他震动了。
是的,这才是绘画艺术真正临境的立体。在他的眼里:只有从平面画,看见艺术本身立体的站立,才是他最渴望得到的形格法相。
尽管,形格修炼的法相锋棱,可以神秘显化在时空间。但是,靛君知道:那就是一根根硬棱拼叠的积木塔。并非一触心机,轰然高耸的、意象瞬间化成的那一个整体。
蒋涵子顿感:侧身站立的靛君斜下俯视自己手中的笔。
顿时,笔辇沉堕着,随势飞来的黑刀一掠,就见一道儿滑过的黑色线条,横削一个平面飞刃。
噌——
蒋涵子那一道运笔刚矗起的一个立体,就飞落一半画质的立体。顿时,画境里,画像的衣袂出现一个模糊的皱褶。
一直随线条流淌的眼神,精意驻留在每一个点,每一条线。即时表达的瞬间,猛然受惊的蒋涵子抬头。
却见石雕眼神,在靛君破坏性的一刀狂风中,潋滟随动的空气流光滑过光迹。
原来,靛君暴烈的凶煞刀风刮过时,消淡了蒋涵子执意表现的线条。
的确,绝对的静哑无论多么生动,也只有在变化的瞬间,才能显示出:那些隐隐埋没在静态中不易发觉的灵性。
就是那道狂蚀风,引动的变化,打破完满保持中的视觉平衡感,让石像画,瞬间于境中显示最敏捷眼睛指津的飞光。
一纤光,瞬间绽露的形、光、色,就是一个生动传神的立体会意。蒋涵子看清了——生命中神秘暗示的“真”。
顿时,那一纤光迹,憾然如,穿透千万年尘封铁锁,破开厚重包绕的坚革。正破开亘古久远的神秘壁垒,响起音声不竭的浩瀚之风。
仿佛从靛君的摧折中站起。蒋涵子并没有因为被黑刀惑扰,像起初那样,将目光瞄向靛君。
他不堪地饮噎一口黑刀拂面的冷风,依然握持铅笔,左手按住胸口狂跳的一颗心,右手还原着:面临石像原契,竭力把稳温柔勾笔的动作。
空间,轰轰响动的乾坤似乎摇晃起来。嗡嗡蜂鸣渐渐让蒋涵子被搅扰的思索,变得快要模糊、膨胀……
靛君的黑刀不断起落着,发狂颠荡起来的风浪,摇曳得蒋涵子仿佛——暴风骤雨的海面上猛颠的孤舟。
画的立方被黑刀一层层削断,又被蒋涵子一笔笔极致温柔的补白。反复修饰同一种形体的枯燥感,重重叠叠打磨掉蒋涵子知觉里,那些即时鲜艳怒放的灵性……
极致悲恸地抬头,看向原契。重复毁灭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的那个自己,仿佛浑身沁透一层层洇染的新旧血迹痂疤——形成的盔甲,带着无尽自卑的耻辱感,走在无极限腥风烈呛的路上,正缓缓修饰那血疤上,一幅画还会经受“罹难”中的温柔工序。
靛君又是一个强大无匹的靛君境了。毁杀的自由,不定向地穿凿——画感最痛苦的地方。那些地方就是意识触碰艺术瞬间,最精敏的灵性。
到处都是失落的痛。到处都是杀戮的黑色光芒……
蒋涵子负痛如负重的的身躯,在只有一个刀的绞痛中,为了锐减肉身、身心、意识、精神……的冗长之痛,用最短时光的感受,收集灵性被逼仄到接近绝境时,洒落在地上的颗粒。
“涵子!笔在这儿……”
“涵子!别打盹……”
“酱哎,倒势会变成……”
“酱哎……”
蒋涵子模糊地应答着耳畔喧嚣的频响,牵强地绽放一个留给自己的苦笑声。
频响飞扬的音铃,立体声波快要环绕地球,百变——屈折语素表达到极端的:清浊破擦与小舌颤音,闪音的顶喉,黏着谐振的华丽尾唱。
无数个只有自己一个人能够看到的刀,无数个立方被削碎堕落的瞬间的不平衡画感,冲击无数个活生生、光鲜、雅静的眼神与表情。
毁坏与成全中,披风穿行在刀光腥风中的画,不停地链接着——其中一个个鲜活瞬间的片段。
时间好久远哦,仿佛自亘古,一直连接了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