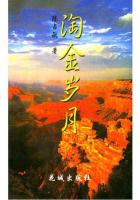萧澈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小的人形木雕给他看:“昨天,玉萱阁的碧媛送我的。”
韦白凑过去一看,花花公子摇着扇子的放浪情态和涎笑真雕刻得惟妙惟肖:“手艺很高明嘛,但,这和我说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萧澈怪声答道:“我该叫碧媛也帮小崔刻一个的!”
韦白失笑,原来他有弦外之音,暗讽某人简直就是木头人一个,于是便仗义执言:“她毕竟是女孩子,而且面对的人又不是普通人,还有她自己现在的身份也……”
萧澈却笑不出来:“想想这事以后会怎么发展?真让人悬心啊。”
“我信得过陛下,他绝不会让小崔吃苦的。”韦白很坚定地说。
萧澈叹气:“不让别人吃苦,自己就要吃苦。还是让别人吃苦好。”
崔捷等人在启夏门外与一千名压着辎重的龙武军士兵会合,正式告别了长安城向东南而去。她回望了一下启夏门,方才离开承天门、朱雀门、远辉门,她都没有回头,这一别,只怕没有两三个月都不能回来。
韦大人和令狐校尉说着话,她悄悄伸手入怀,拿出那瓶向丁洛泉讨来的敷脸的药,放进挂在马鞍上的包袱中。这两天忙着出使前的准备,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不过自己也真傻,刚才那么多人围着,更不可能交给陛下了。
她抬头望望天,目前阳光还不算太炽烈,不敢想象到了正午,在这寸草不生、黄沙滚滚的官道上会是怎样的炙烤,不过包袱里有一大壶丁洛泉昨晚送来的解暑的清茶。
他是这次朝廷紧急征用派往易州的七名大夫之一,自己也是看了名册才知道。
昨晚和他开玩笑:“为什么仁安堂偏把你推出来?是不是得罪人太多了?”
“别人或者上有父母,或者下有妻小,只有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听起来像是主动请缨的呢。
她提醒他:“那儿可是战场,说不定哪天又打起来。”
丁洛泉微笑答道:“你敢去的地方,我没有理由不敢去。”
咦?!回想到这,她的心脏突然怦怦地跳了两下,赶紧用力甩头:“哎,我真是晒昏了,乱想什么呢。”
这趟路程比从酒泉到长安时更觉辛苦,除了炎热,还有接近于急行军的要求。不过韦大人也很体恤士兵,总在必须的时候让大伙儿驻扎休息半天。这么多天相处下来,真觉韦大人和守素不愧是父子,相貌举止谈吐简直相像到了十分,都有让人如沐春风的谦和谨雅。可是,据广文书局送她的那本《登科记又补遗》中说,韦大人的夫人,扶风郡王的女儿高密县主,是长安城著名的三大“母老虎”之一,这么多年都不准他娶妾,理由是:“反正你已有一个儿子了。”
所以嘉川经常很不厚道地在守素面前炫耀自己兄弟多。
所以韦大人不畏辛劳、离京外任或出使的次数比其他人要多得多。
本来以守素的条件,已大大满足很多王公大臣心中理想女婿的标准,但畏于他的母亲,鲜少有人提亲。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常山郡王的女儿淮阳县主在十五岁那年对某次宴会中吹箫助兴的韦家公子一见倾心,发誓非他不嫁,刚好高密县主也曾放话说一定要为儿子娶一位县主媳妇,两边立即一拍即合。
但,那本书又说,不知为何,韦公子婚后似乎就很少吹箫了……
哎,广文书局每月送这么多书籍样本过来,怎么我偏就看了这本呢?尽是些无益的小道消息,说长道短的。不过,自己还是花一个晚上就看完了……真要好好检讨一下。
有一天休息时,韦大人在大树下摆了棋盘请她一起下棋,崔捷欣然从命。开局一会儿,崔捷便断定韦大人棋艺和自己半斤八两,或者不谦虚地说,比自己还差点儿。这盘开局不错,也许能小胜。
再下七八子,韦大人也感觉形势不妙,笑着说:“小崔你等等,我去拿必胜秘籍来。”
崔捷讶然,韦大人跑到他的马儿那边,从包袱里取出一本薄薄的书簿来。
等他回来,她翘首偷看,墨迹似乎还新,里面全是棋谱。韦大人每下一子都要查谱,崔捷心里嘀咕:照本宣科会有用吗?
又下了七八子,崔捷暗暗称奇,局势竟然不知不觉中被扳平了。她抖擞十二分精神应付,终局还是遗憾告负。
她忍不住问:“韦大人,这棋谱是谁编的?好像很厉害啊?”
韦大人呵呵大笑:“哪有厉害,其实是守素写的。他说我多半赢不了你,就编了这个制胜法宝给我,你可别生他气,他怕我输了不高兴呢。”
崔捷傻眼,原来我的棋艺已经烂到可以让人决胜于千里之外了!
她干笑了一声:“守素可真孝顺。”
之后的几次对弈,崔捷一直未尝胜绩,心里不免有点不甘,暗想:叫我别生气,自己拿着棋谱都不肯放呢,分明还是不高兴输嘛!守素真了解自己的爹呢。
这天晚上,大伙儿就在野外扎了营,没有值守任务的人都累得睡了。她就着明亮的月光,对照着韦白的棋谱,在棋盘上摆子。
韦大人竟然如此大方地把棋谱借给她,哎!
她冥思苦想到入了迷,完全没注意到丁洛泉已来到了身边。
丁洛泉声音温和地响起:“怎么还不睡,不累吗?”
她还在深思中,嗫嚅着答:“累啊。你看,这棋谱是专门对付我的呢!”
丁洛泉探头过去看了一阵,把棋谱和她手中的棋子都夺过来:“这好办,我也帮你编一个棋谱,保管你能赢。”
崔捷揉揉眼睛,委屈地说:“你真有办法?”唉,自己平日也没那么大的好胜心的,但这回也太欺负人了不是?
“你想胜几子呢?”
“不要胜很多啊,或者平手就好。”
“交给我好了。放心睡吧,别累坏了。”丁洛泉微笑着笃定地说。
第二天下午,丁洛泉果然就把一本新写的棋谱交到她手上。但在下一次对弈时,可能韦大人已过足了瘾,把棋谱放在了一边,崔捷就凭自己的力量赢了。
等到韦大人再次拿棋谱上阵,崔捷才有机会试试丁洛泉的棋谱是否灵验,最终结果竟然真的是平局。
延英殿内,皇帝翻看着韦从贤等人的奏折,他们辛苦跋涉十五天后终于抵达了易州。
这十五天中,韦从贤共有五道奏折,最近一道更是事无巨细洋洋洒洒数千言禀报了易州目前的情况,便是令狐胜都有两道奏折,而崔捷就只得一道,且寥寥数语,实在有敷衍之嫌。
“陛下?陛下!”康福连叫了两声。
皇帝回过神,放下奏折问:“什么事?”
“司天台通玄院的姚司丞和工部严主事求见,好像是为同一事而来的。”
皇帝笑道:“司天台又有堪舆问题和工部相左吗?让他们都进来吧。”
康福出去领了两拨人进来,皇帝有点诧异,司天台的人趾高气扬,难掩喜色;工部的人神沮色丧,战战兢兢,莫不是被司天台抓住了什么把柄?
姚司丞先发制人道:“陛下,今日工部缮修翰林院时,把门前沙堤铲起,沙丸俱碎。此处格局一坏,只怕要危及众位大学士啊。臣等不可不报。”
皇帝小小一惊:翰林院?
严主事俯首向前膝行三步,颤着声说:“陛下,是臣之过,没有把这么重要的事项告知小匠,恳请陛下降罪。”
皇帝定了定神:“究竟怎么回事?”
姚司丞说:“陛下,太宗皇帝立国之时,决意要偃武修文、尊儒重德,所以初建大明宫,特意命工部把翰林院建于延英殿之西北,以对应天上帝星、文曲星之方位,而门前沙堤正是最紧要之所在。司里一直流传下来的说法,误碎沙丸,则必损翰林。高宗、睿宗朝就是因为这缘故而相继有翰林辞世啊。”
严主事汗如雨下,拼命磕头。
皇帝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天高地远,鬼神之说近乎荒谬无稽,可偏偏有时又十分灵验,令人深畏[1]。
细想翰林院中的学士,最老的也只年过不惑,该不会……皇帝用力握拳:现在那什么沙丸碎都碎了,论罪又有什么意义:“姚卿,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姚司丞和严主事私底下本有些嫌隙恩怨,正想趁机打压,一听这话,就知道皇帝不会追究了,失望得很,却也不敢显露出来。心里兀自冷笑:不知道会应在哪个倒运的翰林身上。
皇帝叫康福:“传令给太常寺,朕从明日起斋戒半月,禁猎一月。”
姚司丞和严主事都跪伏道:“陛下仁厚宽恤,实乃众臣之福。”
因为不是重大的祭天、祭祖前的斋戒,翌日,大明宫昭德寺内,太常寺官员只执行了最简单的仪式,皇帝静心默念了自惩自戒的祝词。太常寺卿把正反两面分别刻着“斋戒”、“敬止”的铜牌锁在皇帝颈上,半月之后才能取下,他口中亦念道:“谨请陛下这段期间戒荤、戒酒,不听乐、不近色、不吊丧、不理刑,腥杀之事宜止之。”
身在千里之外易州古亭县的崔捷不知道宫中发生了这段插曲,他们把七百名士兵留在易州帮忙修筑城墙,她和韦大人、令狐校尉各自分领一百士兵到易州下辖的遂城、安义、古亭视察,向战死士兵家中分发各样赈济物。
连日来住在县衙中,全不见县令升堂办公,安静得连蚊子飞过都能听见,这天暂且抛下公务到外面走走,打听到这位父母官口碑似乎还不错。
走了一会儿,前面有两个孩童追逐打闹,踢翻了水井旁的木桶,那桶咕噜噜地滚到了路中央。崔捷连忙快走几步,俯身提起小桶,放回到水井边。
一抬头,就见到丁洛泉微笑着朝自己走了过来,她轻轻拍手把沾到的尘土掸去,开玩笑道:“夫子曰,不以善小而不为。”
丁洛泉愣了愣,崔捷奇怪地问他:“怎么了?”
丁洛泉笑笑:“没什么,只是突然想起我三弟,他也对我说过同一句话。”难得他主动说起私事,崔捷不禁睁大眼,竖起了耳朵。
丁洛泉见她这么好奇,只好说下去:“就是有一次,我告诉他在外面见到了不平之事,他问我有没有拔刀相助。我答即使帮了这一回,也不能使那种事情销声匿迹的,于是他就对我说了这句话。”他有一丝感慨,“他比我积极,我不如他。”
崔捷小心地说:“其实……你并不讨厌你弟弟的,是吧?”
“我总共也没见过几次面。”丁洛泉想了想,笑中带着苦涩,“看别人兄弟相处就是打架斗气抢东西,但我们不是这样的。”他眼里有些伤感,“我们没那么多时间浪费在打架上。”